$ ?9 n2 B5 o7 F0 U* s6 S醒来,我好痛苦,好难过。父亲一生劳作,活着出力,过世了,我还见他出力。
* Q$ Q! L: V3 z3 ^: P5 n0 e) h$ ?" s+ J2 ], ]& j
父亲八岁开始放猪,大一点放牛放马,后来给地主家当打头的,再后来又给生产队当打头的。他的一手硬活强活令周围十里八村的乡亲们折服,至今仍难以忘怀。
7 C0 y7 q# n8 K6 i
3 H4 p: n$ i: d& M* g7 m
岁月的磨刀石能磨平一切痕迹,但永远也磨不平父亲在我心中的形象。他,高高的个子,肩宽体壮,典型的东北农民。一双粗糙的大手掌里总是茧花常开。晚年的他瘦得筋骨分明,总是咳嗽,那是多年辛苦伤力落下的。但父亲一直没有撂下手里的活,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时至今日,我看到黑土地上劳动的老人们,便会想到父亲,想到他出过的力气,眼泪就止不住了。
5 V! q/ _' I/ B* L
记忆深处唤来的印象要数每天夜半最清晰了:父亲哼哼着醒来,然后是一阵咳嗽。母亲替他捶背,数落他不会悠着劲干活。十几岁的我已有些懂事,睁开圆圆的眼珠儿,又闭上了,一阵阵难受袭来,恨自己长得迟。
, J% q" f- u% }4 b2 s2 O5 F
# ~: `' s6 w/ W
想来,生产队是照顾父亲吧常让他一个人去干零活。如“大帮哄”无法排的“抹斜”、“夹瓣垄”。时间是父亲一个人的,活也是父亲一个人的,父亲什么时候想抽一支烟就抽一支。按说父亲该轻快多了,但每天夜半,他仍哼哼着醒来。一次,从队长跟别人唠嗑里才知道,他说派别人干零活,说不定磨蹭个三天两天的,而派老姚头,一点也不误。原来,父亲一个人干活也总不闲手。我们劝他,他说,人家信着咱了,咱能混?
! y! J( C( V- n+ D# [: ]) w
/ O% \/ ~# L) k- P& A
我开始在大队里有点权力了,我悄悄地运用我的影响。我跟队长说,安排老爷子去积积肥吧。现在想起来,跟着一头瘦得不能再瘦的老牛拉着一台破胶皮轱辘车,其实就是将就这些本该撂下活却撂不下的老人们,给他们退到“二线”的机会,或说白了,是“大锅”就将就他们一碗饭吃。
; F4 [( b0 V2 [9 t2 [' Y
7 s' ~; H4 F1 K" N7 m f1 e0 u8 ~
可是,父亲去积肥后,半夜时还是累得哼哼着醒来……
0 X' ]& c% M1 e2 t3 r8 z0 V: j" I
! a- p- p( \3 v. v9 r
我暗暗地注意父亲干活。见他一锨接一锨地往车上装粪,还像以前一样。晚上,我告诉他,“爹,到岁数的人,活不能那么干。”他笑一笑说:“我也没怎么干,就是不行了。”我说:“你没见王二叔,扔几锨拄一会儿,多缓劲,你就不会藏藏尖儿”如此多次,父亲说:“开始也想缓缓劲,但干着干着就忘了,唉,干死手了。”
j) z0 n, n1 E* i+ P P" Y# U) J+ ?% Z A
父亲实实在在地干了一生,习惯了,经我这劝说,也曾有过藏尖儿的念头,但终藏不成。而我们闲散惯了,虚虚假假惯了,也就看不惯实实在在的干了,以至把父辈的实干看成了可悲。
9 Z6 y u! z; U+ E) h F
! }7 j# {( W' e2 o" v
父亲一生只照过一次像,还是黑白的。那是身体不行的时候,队里安排他看菜地,他坐在田头上,镜头的延伸处,便是肥沃的黑土地和碧绿的白菜……父亲的形象永远雕在黑土地上了。
5 U( m7 x$ \2 k$ s. o! C) [
3 P: @: ?3 E1 v$ g. h% v
我在照片后面写了这么几句:父亲总是搓他那宽阔的胸脯,泥总也搓不尽……我想,父亲的胸脯就是这肥沃的黑土地吧!
2 L3 |8 u! q+ q) 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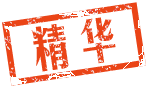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