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宗亲,注册并登录姚网后才可以发帖,才可以结交更多姚氏宗亲。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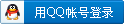
x
(明·馮從吾撰)《少墟集》 卷三 讀《論語》下 問: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不知何所為而能若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顔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可見問之一字,乃舜之所以為舜處,亦囘之所以希舜處。 舜雖遭父頑弟傲,自舜視之不知其為頑為傲,只知道自家要孝要弟,所以為古今大聖。此所以孟子論三自反,必引舜為法。 妄人禽獸云云,君子到三自反後,才好如此說,此是究竟盡頭的話,不是輕易說的。此所以下文緊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又引舜以為証,若謂必自反如舜而後可以言自反,而後可以言不校耳。舜不是容易如的,妄人禽獸不是輕易說的。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自古聖賢相傳正脉。堯、舜以此帝,湯、武以此王,伊、周以此相,孔、孟以此師,自古及今,此脉常在,人皆可以為堯、舜,正在於此。第堯、舜能知擴而充之,故可以保四海;途人不知擴而充之,至於不能事父母。夫父母至親也,而至於不能事,又何論民物?然其所以不能事父母者,乃不知擴而充之之過,非本來無此心也,或者至此不免於疑而不信,故孟子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驗之。夫世豈有孩提而不知愛,稍長而不知敬之人乎?堯、舜此心,途人亦此心人,皆可以為堯、舜,誠可以深信而無疑矣。知愛知敬之心人原皆有之,而不驗之孩提稍長,則人不信其皆有,此孟子不得已提醒人心處,識得此心便是仁,擴充得此心便是為仁,遇親而親莫知其所以親,遇民而仁莫知其所以仁,遇物而愛莫知其所以愛,總之從此知愛知敬一念中流出。故曰堯、舜其心至今在此,自古聖賢相傳之正脉,誠不在語言文字間也。吾輩為學,正當在此處識取方可。 卷七 寳慶語録 又問:堯、舜,地步最高,功業最偉,及閲子輿氏論,一不為堯隔壁即桀,一不為舜隔壁即蹠,夫堯桀、舜蹠相去霄淵,何故並談無别?曰:堯之隔壁就是桀,舜之隔壁就是蹠,中間再不隔一家,此孟子所以並談無别。世之學者既不敢為堯為舜,又不甘為桀為蹠,只是錯認以為中間尚隔許多人家耳。使早知堯之隔壁就是桀,舜之隔壁就是蹠,自然一步不敢差錯。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孝?如何弟?安能孝弟?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若不講,如何忠?如何恕?安能忠恕?彼謂只孝弟忠恕而不必講者,是原無心於孝弟忠恕者也。 卷八 《善利圖》説 或問:孟子,願學孔子者也。孔子論人,有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之别,而孟子乃獨以善、利一念分舜、蹠兩途,何也?曰:此正孟子善學孔子處。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列為四等,正所以示入舜之階基,恐學者躐等而進耳。世之學者徒知以舜、蹠分究竟,而不知以善、利分舜、蹠,若曰聖人至舜極矣,學者何敢望舜下聖人一等,吾寧為君子已耳。或者又曰君子我亦不敢望,吾寧為善人已耳。或者又曰善人我亦不敢望,吾寧為有恒已耳。上之縱不能如舜,下之必不至如蹠,何苦呶呶然曰吾為舜吾為舜哉?以彼其心,不過以為聖人示人路徑甚多,或亦可以自寛自便耳,不知發端之初一念而善便是舜,一念而利便是蹠,岀此入彼,間不容髮,非舜與蹠之間復有此三條路也。君子、善人、有恒造詣雖殊,總之是孶孶為善大舜路上人,孟子以善、利分舜、蹠,蓋自發端之初論也;孔子以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分造詣,蓋自孶孶為善之後論也,旨豈二乎哉?雖然,為衆人易為聖人難,故學者儘學聖人,尚恐不能為君子、為善人、為有恒,若姑曰我寧為君子,我寧為善人,我寧為有恒,其勢不至於無恒不止,不至於如蹠不止也。何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取法乎中民斯為下,理固然也。究其初心,豈非錯認路徑,尚多之一念誤之哉!且為善為舜則為人,為利為蹠則為禽獸,所係匪細,故又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玩幾希二字,可見人必至於如舜,如禹,如成湯,如文、武、周公,孔子纔謂之君子,存之纔謂之人,不然庶民去之則禽獸矣,善、利之分舜、蹠之分,舜、蹠之分人與禽獸之分也。學者縱可諉之曰我不為聖,亦可諉之曰我不為人哉?或曰:一念而善為舜為人,一念而利為蹠為禽獸,固矣,倘學者不幸分辨不蚤,誤置足於蹠利之途,將遂甘心已乎?曰:不然。不聞孟子山木之章乎?蓋人性皆善,雖當伐之之後而萌蘖尚在,故曰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又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夫以斧斤伐之之後,而尚有此幾希之萌蘖,養此幾希之萌蘖,而尚可以為堯、舜,人奈何以一時之錯而遂甘心已乎?幾希二字,正是孟子提醒人心死中求活處。或又曰:養此幾希尚可為舜,固矣,彼牿之反覆夜氣不存者,獨無一線生路乎?曰:有觀孟子不曰夜氣不足以存即為禽獸,而猶曰違禽獸不逺,謂之不逺尚猶有一線生路在,若謂斯人也縱不能每日有平旦之氣,而數日之中亦未必無一時之萌蘖,使從此一時之萌蘖,囘心而向道,則牛羊猶可及止耳,豈真不可救藥哉?惜乎人之諱疾忌醫,終身自伐自牧而不知自悔也,悲夫!或又曰:幾希之説,蓋為誤走蹠路者發也,若幸走舜路者,可遂以舜自命而不復求進乎?曰:不然。一念而善,是平地而方覆一簣也;一念而自以為善,是為山而未成一簣也。夫未成一簣且不可,況半塗而廢者乎?孔子列有恒、善人、君子、聖人之等,正使學者循序而進,毋半塗而廢耳,非以君子、善人阻其進也。且謂之曰有恒,必由一簣而為山纔謂之有恒,若以善人、君子中止而不至於聖人,總謂之半塗,總謂之無恒,此孔子所以惓惓致意於有恒也。道、二之説,善、利之説,欲人慎之於其始;半塗之説,為山之説,又欲人慎之於其終。聖賢憂世之心見乎辭矣。或又曰:世之聰明之士非乏也,功名文學之士又不少也,豈見不及此,而舜、蹠云云不亦過乎?曰:不然。舜、蹠路頭容易差錯,此處不差,則聰明用於正路,愈聰明愈好,而文學功名益成其美;此處一差,則聰明用於邪路,愈聰明愈差,而文學功名益濟其惡。故此處不慎,而曰某也聰明,某也功名,某也文學,何益哉?何益哉?或者唯唯。余因作《舜蹠善利圖》,而為述其説如此云。 附錄 問: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又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不知自家一人,安能必得大家?余曰:然。彼世之自家要做君子做善人,而不要大家做君子做善人者,抑豈能以自家一人必得大家乎?自家一人不能必得大家,而却要大家不為君子不為善人,勢必不能,徒以自壞其心術,自得罪於天地鬼神而已矣。學者固不能必得大家都做君子做善人,而這一念必不可無,有此一念便是善,無此一念便是利,故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又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初學之士,儘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尚不能,以父母兄弟妻子奴僕為一體,若藉口於兼愛之非,而不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則其流弊,又當何如?孟子曰孳孳為善者舜之徒,又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是孳孳為善者為其與人同者也,不為其所以與人同者,而徒曰我為善我為善,是舜之善如彼而我之所以為之者又如此也,天下豈有兩様善之理,其何以為舜之徒哉?大約叔季之世,自私自利之風浸淫已久,為不善者無論,即為善者孳孳,到底强半已成就得一箇自私自利。且如平日看書,與朋友講論時,凡及於己立己達一邊話説便覺耳順,便覺津津有味,更不説恐流於楊氏為我;凡及於立人達人一邊話説,便覺耳逆,便覺意思不合,即説恐流於墨氏兼愛,如門人之疑羅近溪者,蓋不少也。不知其恐處正是病處,如曰不是病處,何為不恐其流於為我而獨恐其流於兼愛也。如此病根浸淫已久,併自家亦不知不覺耳。此根不拔,則聞見愈廣講論愈多,其病痛愈深。譬之病寒者復用硝、黄,病熱者復用薑、桂,豈徒無益而已哉?宜乎反為不用藥者之藉口也。吕與叔云:克己功夫未肯加,吝驕封閉縮如蝸;試於夜氣深思省,剖破藩籬即大家。此先儒已試之良方,所以藥天下萬世於無窮者也。學者倘有意於善利之辨,不可一日不三復是思。 人人能克去私、己二字,便是青天白日心腸,便是海闊天空度量,便是光風霽月襟懐,便是天清地寧世界。何等瀟灑,何等快樂,故曰善,故曰舜之徒。 卷十四 做人說下 館中與二三同志論學,彼此拳拳,以做人相印證。余曰:做聖人易做文人難,吾儕於難者尚殫精竭力圖之於易,於易者反玩日愒月委之於難,何也?或有疑者,欲余竟其説。余曰:難易之間是在自悟,非可以騰諸口説也。無已,試以舜、孔觀之。古今論大聖必曰舜、孔,舜之德業詳載《虞書》,中若不可幾及,而夫子乃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隠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玩“其斯”二字,可見《虞書》所載多少德業,都不是舜之所以為舜處,而惟此乃其所以為舜。然則好問好察難邪?隠惡而揚善難邪?孔子天縱聖人不知有何様高逺之為,而其自道,第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夫發憤忘食難邪?樂以忘憂難邪?由此觀之,吾儕特不肯去把做詩文之心為做聖賢之心耳,若是肯去好問好察,肯去隠惡揚善,肯去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則舜、孔有何難為?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陽明先生曰:箇箇人心有仲尼。豈欺我哉?吾儕祇説堯、舜、孔、孟難為,試觀一日十二時中,曾去好問好察否?曾去隠惡揚善否?曾去發憤忘食曾得樂以忘憂否?途患不行不患不至,不用工夫而曰堯、舜、孔、孟難為,真難之難也。且吾儕自入館來,朝而誦,夕而諷,行思坐想,何嘗一息不在詩文上用功,其詩文何嘗一息不在班、馬、李、杜上模擬,真可謂殫精竭力矣。試自反之其詩文,視班、馬、李、杜竟何如邪?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僉以為然。余又曰做人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言已多矣。願相與共朂之。 孝弟說别孫生繩祖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又止為士之次,何也?蓋堯、舜之孝弟,是造道之極滿,孝弟之量者也。鄉黨宗族之稱孝弟,如王祥、王覽輩是天資之美,盡孝弟之一節者也。盡孝弟之一節即可以為士,可見人皆可以為堯、舜,祇是人安於天資之美,未加學問之功,安於一節之善,未滿分量之全,所以為士之次,所以堯、舜不可為耳。豈堯、舜之道有出於孝弟之外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士,是原泉混混之水也;堯、舜之孝弟,則放乎四海矣。堯、舜雖放乎四海,其實不過滿其原泉之量,又未嘗於原泉混混有所增加,故曰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華下孫生繩祖,幼而失怙,垂髫學舉子業,弱冠王母歾,生宜承重,哀毁逾禮。既襄事,廬於墓側者三年,一時以孝聞。戊申春,余偕同志講學太華山中,而生偕其師劉生若魯、友李生華實、王生國賔,徒步九十餘里從余遊。瀕别,余朂之曰:若不聞田畫之告鄒志完乎?願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為者未止此也。生聞其言,再拜而謝。明年己酉三月,生復徒步二百餘里,從余講學太乙峰下,余留居月餘,見其氣宇端凝,意向勤懇,視昔益有加焉,此其所造將來蓋未可量者。余深喜吾道之得人也,因其歸,書孝弟説以遺之。 |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