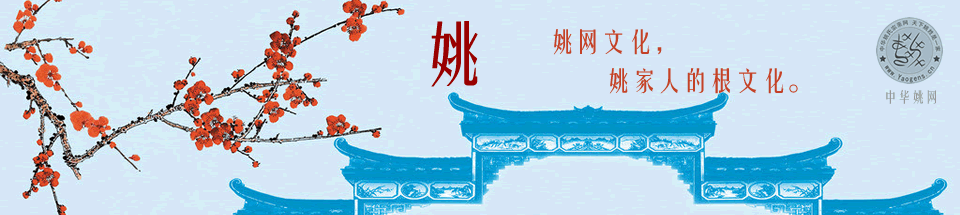(清·崔述撰)《古文尚書辨僞》
(清·崔述撰)《古文尚書辨僞》 恭錄《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尚書》三則(編點者按: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提要、毛奇齡《古文尚書冤詞》提要已分别收在閻氏、毛氏二書之前,此略)《尚書正義》提要《尚書正義》二○卷,舊本題漢孔安國傳。其書至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於朝。唐貞觀十六年,孔穎達等爲之疏。永徽四年,長孫無忌等又加刊定。孔《傳》之依託,自朱子以來遞有論辨,至國朝閻若璩作《尚書古文疏證》,其事愈明。其灼然可遞者,梅驚《尚書攷異》攻其注《禹貢》“瀍水出河南北山”一條,“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一條,地名皆在安國後。朱彜尊《《經》義攷》攻其注《書序》“東海、駒驪、扶餘、馯貊之屬”一條,謂駒驪王朱蒙至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安國,武帝時人,亦不及見。若璩則攻其注《泰誓》“雖有周親,不如仁人”,與所注《論語》相反。又安國《傳》有《湯誓》,而注《論語》“予小子履”一節,乃以爲《墨子》所引《湯誓》之文(案安國《論語注》今佚,此條乃何晏《集解》所引)。皆證佐分明,更無疑義。至若璩謂定從孔《傳》以孔穎達之故,則不儘然。攷《漢書·藝文志》敘《古文尚書》,但稱“安國獻《尚書傳》,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始增入一“傳”字,以證實其事。又稱“今以孔氏爲正”,則定從孔《傳》者乃陸德明,非自穎達。惟德明於《舜典》下注云:“孔氏《傳》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又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方興本或此下更有‘睿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則開皇中雖增入此文,尚未增入孔、興中,故德明云爾。今本二十八字當爲穎達增入耳。梅賾之時,去古未遠,其“傳”實據王肅之注而附益以舊訓,故《釋文》稱:“王肅亦注今文,所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此雖以末爲本,未免倒置,亦足見其根據古義,非盡無稽矣。穎達之疏,晃公武《讀書志》謂因梁費彪《疏》廣之。然穎達原序稱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六家,而以劉焯、劉炫最爲詳雅,其書實因二劉,非因費氏。公武或以《經典釋文》所列“義疏”僅彪一家,故云然與?《朱子語錄》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爲下。其言良允。然名物訓故,究賴之以有攷,亦何可輕也! 《古文尚書辨僞》卷之一《古文尚書》真僞源流通攷僞《古文尚書》之成立唐、宋以來,世所傳《尚書》凡五十八篇:其自《堯典》以下至於《秦誓》三十三篇,世以爲今文《尚書》;自《大禹謨》以下至於《冏命》二十五篇,世以爲《古文尚書》。余年十三,初讀《尚書》,亦但沿舊說,不覺其有異也。讀之敷年,始覺《禹謨》、《湯誥》等篇文義平淺,殊與三十三篇不類,然猶未敢遽疑之也。又數年,漸覺其義理亦多刺謬,又數年,復漸覺其事實亦多與他《經》、《傳》不符,於是始大駭怪,均爲帝王遺書,何獨懸殊若此?乃取《史》、《漢》諸書覆攷而細核之,然後恍然大悟,知舊說之非是。所謂《古文尚書》者,非孔壁之《古文尚書》,乃齊、梁以來江左之僞《尚書》;所謂今文《尚書》者,乃孔壁之《古文尚書》也。今文《尚書》者,伏生壁中所藏,凡二十八篇(後或分爲三十一篇),皆隸書,故謂之今文;與今《堯典》以下三十三篇,篇目雖同而字句多異。《古文尚書》者,孔氏壁中所藏,皆科斗字,故謂之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得多十六篇。其二十八篇,即今《堯典》以下三十三篇,原止分爲三十一篇,馬融、鄭康成之所注者是也。其十六篇,殘缺不全,絕無師說,謂之《古文尚書》逸篇。西漢之時,今文先立於學官。迨東漢時,古文乃立。自是學者皆誦古文,而今文漸微。永嘉之亂,今文遂亡,古文孤行於世。僞《尚書》者出於齊、梁之間而盛於隋世,凡增二十五篇;又於三十一篇中別出《舜典》、《益稷》兩篇;共五十八篇,有《傳》及《序》,僞稱漢孔安國所作。唐孔穎達作《正義》,遂黜馬、鄭相傳之真《古文尚書》,而用僞《書》、僞《傳》取士。由是學者童而習之,不復攷其源流首尾,遂誤以此爲即《古文尚書》,而孔壁古文之三十一篇反指爲伏生之今文,遂致帝王之事跡,爲邪說所淆誣而不能白者千有餘年。余深悼之,故於《攷信錄》中逐事詳爲之辨,以期不沒聖人之真。然恐學者狃於舊說,不能攷其源流,察其真僞,循其名而不知核其實也,故復溯流窮源,爲“六證”、“六駁”,因究作僞之由,並述異真之故,歴歴列之如左,庶僞者無所匿其情云爾。 六證之一:孔安國古文篇數一.孔安國於壁中得《古文尚書》,《史記》、《漢書》之文甚明,但於二十九篇之外復得多十六篇,竝無得此二十五篇之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史記·儒林列傳》。《漢書》文同,不復舉《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壊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壊。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攷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漢書·藝文志》按:二十九篇者,《堯典》(今《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內)、《臯陶謨》(今《益稷》篇在內)、《禹貢》、《甘誓》、《湯誓》、《盤庚》(三篇合爲一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笵》、《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在內)、《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並序爲二十九篇,與今文篇數同,《史記》所謂“以今文讀之”者是也。其十六篇,《舜典》、《汨作》、《九共》(後或分爲九篇,故《正義》謂之二十四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允徵》、《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史記》所謂“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者是也。而今所傳二十五篇,則有《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有六篇,而無《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五篇;惟《舜典》等十有一篇,與漢儒所傳篇目同,而《舜典》、《益稷》又皆自《堯典》、《臯陶謨》分出,非別有一篇。篇目既殊,篇數亦異,其非孔壁之書明甚。使孔壁果得多此二十五篇,班固何以稱爲十六篇,司馬遷何以亦云十餘篇乎?蓋撰僞《書》者聞有五十八篇之目(劉向《別綠》云五十八篇,蓋分《盤庚》爲三篇,《九共》爲九篇,出《康王之誥》,而增河內女子之僞《泰誓》三篇也),不知其詳,故撰此二十五篇,而別出《舜典》、《益稷》二篇,以當其數。惜乎學者之不察也! 六證之二:東漢古文篇數一.自東漢以後傳《古文尚書》者,杜林、賈逵、馬融、鄭康成諸儒,歴歴可指,皆止二十九,竝無今《書》二十五篇。杜林,茂陵人,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愛之。每遭困阨,握抱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邪!”建武初,東歸,徵拜侍御史。至京師,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皆推服焉。濟南徐兆始事衛宏,後皆更從林學。林以所得《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爲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邪!是道不墜於地矣!”《後漢紀·光武帝》第八卷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後漢書·儒林傳》《尚書》十一卷(馬融注),《尚書》九卷(鄭玄注),《尚書》十一卷(王肅注)。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達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隋書·經籍志》按:王莽之末,赤眉焚掠,典籍淪亡略盡,是以杜林死守此《書》以傳於後。其二十九篇者,即《史記》所謂“以今文讀之”,《本紀》、《世家》之所引者是也。馬、鄭皆傳杜林之《書》,而止二十九篇,然則非但《仲虺之誥》等十有六篇爲古文所無,即《大禹謨》等九篇亦非杜林、賈達所傳之古文矣。如果二十五篇出於孔壁,《經》、《傳》歴歴俱全,何以杜林漆《書》無之,賈、馬、鄭諸儒皆不爲之傳注乎?然則二十五篇決非安國壁中之《書》,明矣。 六證之三:僞書文體一.僞書所增二十五篇,較之馬、鄭舊《傳》三十一篇文體迥異,顯爲後人所撰。《大禹謨》與《皐陶謨》不類,篇末誓詞亦與《甘誓》不類。《五子之歌》、《胤徵》摭拾《經》、《傳》爲多,其所自撰則皆淺陋不成文理。《泰誓》三篇,誓也,與《湯誓》、《牧誓》、《費誓》皆不類。《仲虺之誥》、《湯誥》、《武成》、《周官》,皆誥也,與《盤庚》、《大誥》、《多士》、《多方》皆不類。《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旅獒》,皆訓也,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無逸》、《立政》皆不類。《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陳》、《畢命》、《君牙》、《冏命》九篇,皆命也,與《顧命》、《文侯之命》皆不類。按:《皐陶謨》高古謹嚴,《大禹謨》則平衍淺弱。湯、牧二《誓》和平簡切,《泰誓》三篇則繁冗憤激,而章法亦雜亂。《盤庚》諸誥,詰曲聱牙之中具有委婉懇摯之意;仲虺三誥則皆淺易平直。惟《武成》多摘取《傳》、《記》之文,較爲近古,然亦雜亂無章。訓在商者簡勁切實,在周者則周詳篤摯,迥然兩體也,而各極其妙。《伊訓》、《太甲》諸篇,在《肜日》、《戡黎》前數百餘年,乃反冗泛平弱,固已異矣;而《周書》之《旅獒》乃與《伊訓》等篇如出一手,何也?至於命詞九篇,淺陋尤甚,較之《文侯之命》,猶且遠出其下,況《顧命》乎!且三十一篇中命止二篇,而二十五篇命乃居其九,豈非因命詞中無多事跡可敘,易於完局,故爾多爲之乎?試取此二十五篇與三十一篇分而讀之,合而較之,則黑白判然,無待辨者。無如世之學者自童子時即連屬而讀之,長遂不復分別,且多不知其孰爲馬、鄭所傳,孰爲晉以後始出者,況欲其較量高下,分別真僞,此必不可得之數也。其亦可歎也夫! 六證之四:《史記》引《尚書》一.二十九篇之文,《史記》所引甚多,竝無今《書》二十五篇一語。《五帝本紀》,《堯典》之文(《舜典》“慎徽五典”以下在內)全載。《夏本紀》,《禹貢》、《皐陶謨》(《益稷》在內)、《甘誓》之文全載。僞書之《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徵》三篇,無載其一語者。《殷本紀·宋世家》,《湯誓》、《洪範》(今在《周書》中)、《高宗肜日》、《西伯戡黎》之文全載,《微子》載其半,《盤庚》略載大意。僞《商書》凡十篇,無載其一語者。《湯誥》頗載有數十言,乃今僞《書》所無。《周本紀·魯世家》,《牧誓》、《金縢》之文全載。《無逸》、《呂刑》、《費誓》皆載其半。《多士》、《顧命》(《康王之誥》在內)略載大意。《燕世家》之《君奭》,《衞世家》之《康誥》、《酒誥》、《梓材》,《秦本紀》之《秦誓》,皆略載大意。僞《周書》十二篇,無載其一語者。按:真《古文尚書》二十八篇,《史記》全載其文者十篇,載其半者四篇,略截其大意者八篇;其未載者,《周書》六篇而已。蓋此十四篇者,誥體爲多,文詞繁冗而罕涉於時事,故或摘其略而載之,或竟不載,從省文也,然所載者亦不可謂少矣。僞《書》二十五篇乃無一篇載者,何也?《皐陶謨》載矣,《大禹謨》何以反不載?《甘誓》、《湯誓》、《牧誓》皆載矣,《泰誓》何以獨不載?《呂刑》,衰世之法,猶載之;《周官》,開國之制,而反不載。至於《武成》乃紀武王伐商之事,尤不容以不載。然則司馬氏之未嘗見此《書》也明矣!夫遷既知有古文而從安國問故矣,何以不盡取而觀之?安國既出二十八篇以示遷矣,即何吝此二十五篇而秘不以示也?然則此二十五篇之《書》不出於安國,顯然易見。惜乎後儒之不思也! 六證之五:《漢書·律曆志》引《逸書》一.十六篇之文,《漢書·律曆志》嘗引之,與今《書》二十五篇不同。《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漢書·律曆志》《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於徵伐紂。”“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 “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甲戌,武王燎於周廟。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於周廟。”並同上《尚書》逸篇二卷。《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攷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隋書·經籍志》按:《漢志》所引《伊訓》、《武成》之文皆與今《書·伊訓》、《武成》不同,則今之《伊訓》、《武成》非孔安國壁中之《書》明矣。《伊訓》、《武成》既非孔壁古文,則《大禹謨》等七篇亦必非孔壁古文矣。況《仲虺之誥》等十有六篇乃孔壁之所本無者乎!蓋所得多之十六篇,文多殘缺難解,故《漢志》雖間有徵引,而學者皆罕所誦習,馬融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者也。既無師說,則日益以湮沒,是以迨隋僅存二卷,至唐以僞《書》取士,人益不復觀覽,遂並此二卷而亡之耳。由是言之,《尚書》逸篇即馬融之“逸十六篇”,劉歆、班固所引《伊訓》、《武成》之文,此乃孔壁之真古文,而二十五篇爲後人所僞撰,不待言矣。 六證之六:東漢、吳、晉諸儒道《逸書》一.自東漢逮於吳晉數百餘年,注《書》之儒未有一人見此二十五篇者。《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注:“《書》,《尚書》逸篇也。”趙岐《孟子》注《書》曰:“湯一徵,自葛始。”《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注:“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同上《書》曰:“洚水警余。”注:“《尚書》逸篇。”同上《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兌當爲說字之誤也。高宗夢傅說,求而得之,作《說命》三篇,在《尚書》。今亡。”鄭康成《學記》注《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注:“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鄭康成《坊記》注《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鄭康成《緇衣》注《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注:“《夏書》,《逸書》也。”韋昭《國語》注《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壊!”注:“《逸書》。”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注:“《逸書》。”同上《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注:“《周書》,《逸書》。”同上右十則,皆見於今僞《書》,而趙、鄭、韋、杜諸儒皆注以爲“《逸書》”,或云“今亡”。然則自漢逮晉,無一人之見此《書》也。無一人見此《書》,則此《書》不出於安國明矣。此四《書》中所引《尚書》之文尚多,不可悉載,姑舉數則,以見其凡。孔氏《正義》云:“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竝不見孔《傳》。劉歆作《三統曆》,引《泰誓》、《武成》,竝不與孔同。賈逵奏《尚書疏》,與孔亦異。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竝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竝云‘夏桀時作’,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篇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余按:自孔安國以後學之博者,西漢無過向、歆,東漢無過趙、班、賈、馬、服、鄭,吳,晉無過韋、杜,之數人者皆不見,天下豈復有見此《書》者!藉令安國果有此《書》,一人偶未之見,遺之可也,必無四百年中博學多聞之士竟無一人見之之理。然則當時原無此《書》,而此《書》爲後人所僞撰,不待言矣。 傳僞《書》者之自解五說據此六端觀之,此二十五篇者乃後人所僞撰,非孔壁中之《書》,不待明者而知之矣。然自隋、唐以來,學者皆信之而不疑,何也?蓋緣傳僞《書》者恐人之不之信,巧爲之詞,曲爲之解,學者不復攷其源委,遽信以爲實然故也。其說大抵有五。其一謂馬、鄭所傳乃《今文》,非《古文》,故與伏生之篇數同而無二十五篇,由是學者遂真以三十一篇爲今文,而不復疑此《書》晚出之非真矣。其二謂今文乃伏生之女所口授,因齊音難曉,而晁錯以意屬讀之者,故多艱澀難解,不若二十五篇平易,由是學者遂真以三十一篇爲口授,而不復疑此《書》文體之不類矣。其三因《漢書》有張霸僞作百兩篇一事,遂誣《漢志》所載安國多得篇目乃霸僞《書》之目,所引《伊訓》、《武成》篇文乃霸僞《書》之文,由是學者遂不復疑東晉以後出者非真,而反謂西漢之時得者爲僞矣。其四因《漢書》有“武帝末未列學官”一語,遂誣終漢之世不列學官,以故不行於世,儒者皆不之見,由是學者遂不復疑此《書》爲晉以後之《書》,而反謂司馬、趙、鄭、韋、杜諸儒爲未嘗學問矣。至其尤誣妄者,《正義》引《晉書》云“皇甫謐於姑子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又引《晉書》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宏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由是學者遂以此二十五篇爲真有所傳,而不復疑其爲後人之僞撰矣。而豈知其莫非子虛烏有之事也哉!嗟夫!兩漢、晉、隋之書昭然在耳目間,非天下之秘書世所不經見也,何爲皆若不見不聞然者,而惟僞說之是信乎?故今復采漢、晉諸書之文足證其僞妄者,列之左方,學者一一核之可矣。 六駁之一:《古文》、《今文》篇第不異一.《古文》、《今文》分於文字之同異,不分於篇第之多寡。馬、鄭所傳雖止二十九篇,與《今文》同,而文字則與《今文》異,兩漢之書所載甚明。
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爲《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爲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漢書·藝文志》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後漢書·儒林傳》
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於《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命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後漢書·賈逵傳》
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竝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隋書·經籍志》
按: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皆《今文》也。劉向以《古文》校之而有異文脫簡,賈逵又撰三家與《古文尚書》同異,則劉、賈所見者真《古文》也。若仍是《今文》,則與三家有同而無異,何有異文脫簡?又何撰同異之有哉?是以《尹敏傳》云:“初習歐陽《尚書》(即今文),後受《古文》。”東漢所謂《古文》之非《今文》,明矣。況永嘉之亂,《今文》已亡,安得復有存者!後世學者不知《古文》、《今文》之分,乃以篇數多者爲《古文》,少者爲《今文》,遂以今《書》三十三篇爲《今文》,謬矣!孔氏《正義》稱劉向作《別錄》不見孔《傳》,後世耳食者遂以爲劉向未見《古文》。夫劉向以《古文尚書》核《今文》,若不見《古文》,以何校之?然則劉向但見真《古文》,未見僞《古文》耳。且云“中古文”,則安國之《古文尚書》已上於朝矣,安有藏於家之事!然則馬、鄭相傳之《尚書》,決爲《古文》而非《今文》明矣。
六駁之二:《今文》亦壁藏
一.無論馬、劉所傳之爲《古文》而非《今文》也,即伏生之《今文》亦其壁中所藏之《書》,並無其女口授之一事,不得與二十五篇文體互異。
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漢書》無此八字而有“張生爲博士”五字)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史記·儒林列傳》。《漢書》略同,但文異者十餘,增者一,刪者十餘耳。故不重錄。
按此文,則伏生之《今文》乃壁中所藏《書》。故劉歆《移博士書》亦云:“《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則是二十九篇之策現存,錯何難自以目覽之,而必待夫女子之口授乎?且云伏生能“治”《尚書》而不云能“誦”《尚書》,則是所以欲召之者,謂伏生能通達其義,非徒誦其文也。錯所受者《尚書》之義,烏用以意屬讀?若徒誦其文,則伏生之門人若張生、歐陽生等衆矣,何人不可以授,又不必其女而後能授也。由是言之,伏生竝無口授之事。此二十五篇之所以淺近易知,而與馬、鄭相傳之《尚書》大不類者,正以其作於魏、晉之後,原非二帝、三王之《書》故爾,無他故也。蓋作僞《書》者目知其文不類,而恐人之譏己,故僞造此說以彌縫之。乃後之學者沿訛踵謬,皆信之而不疑,豈《史記》、《漢書》唐以後之人皆不復觀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更從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後漢書·儒林傳》
按:此文言作《訓旨》而不言作《序》。言作《毛詩序》而不言作《尚書序》,則世所傳宏《序》非宏所自作也。孔安國之作《書傳》與《序》,班固不知,則巧爲之說,曰書未行於世也。今蔚宗乃宋元嘉時人,梅賾果於東晉奏上其書,宏《序》行於世矣,蔚宗何以亦不之知?且云“宏受《古文尚書》,由是《古文》大興”,然則宏果有序,班固見之熟矣,何以爲《儒林傳》乃絕不載伏生口授之事,而仍錄《史記》之文乎?蓋由作僞《書》者自知其文不類而恐人之譏己,是以造爲此說,托之孔、衛以彌縫之。乃後之學者沿訛踵謬,皆信之而不疑,豈《史記》、前後《漢書》唐以後之人皆不復觀乎?真天下之怪事也已!
六駁之三:班固斥張霸僞《書》
一.張霸之僞《書》乃百二篇,并非二十四篇,班固《漢書》業已斥之,必無反以僞《書》爲《古文》之理。
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竝。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竝謀反,乃黜其書。《漢書·儒林列傳》
按:《漢書》此文稱霸書“文義淺陋”,又云“以中書校之非是”,是班氏明明以張霸之書爲僞矣;烏有作《儒林傳》則痛詆其僞,作《藝文志》又深信其真,作《律曆志》反引其書爲證者哉!班氏所引《伊訓》、《武成》之文,非霸僞書而爲孔壁之真《古文》明矣。《漢書》所引者爲真,則梁、陳所出者爲僞可知也。況霸所撰乃百二篇,非二十四篇;乃分析二十九篇爲之,亦非別有二十四篇也。今穎達但欲表章僞《書》,遂公然以安國以來相傳之逸十六篇(即二十四篇)爲僞,復公然以百二篇爲二十四篇,亦妄之至矣!且十六篇之語不始於固,《史記·儒林傳》言之矣。司馬遷,漢武帝時人,張霸,成帝時人,遷作《史記》,何由預知後世之有張霸僞《書》,並其篇第之多寡乎!蓋凡穎達之說,顛倒矛盾,類皆如此。學者少留意焉,則其謬不攻自破矣。
六駁之四:《古文尚書》立學官
一.孔安國《古文》,當時已傳於世,王莽及章帝時又已立於學官,兩漢之書所載甚明,並未散軼,不容諸儒皆不之見。
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榖梁春秋》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爲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漢書·儒林列傳》
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榖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羡慕焉。《後漢書·賈逵傳》
按此文,則《古文尚書》當孔安國時已傳於人而行於世,至王莽時而立於學官,至東漢章帝時而再立於學官,且爲帝所崇重,習《古文》者畢授官,而爲世欣欣慕矣,安得諸儒皆不之見,至梁、陳時而突出乎?蓋《漢志》所謂“未列於學官”者,謂未置博士及弟子耳,非謂其《書》不行於世,但藏於家也;謂武帝時未列於學官耳,亦非終已不列於學官也。且《毛詩》、左氏、榖梁《春秋》當武帝時皆未列於學官,皆至王莽時而始立,至章帝時而再立,何以皆行於世,馬、鄭、服、杜皆得見之而箋注之,獨《古文尚書》遂以不列學官之故,致無一人之見之乎?甚矣不學而耳食者多也!
六駁之五:《晉書》無《古文》授受事
一.《正義》稱鄭沖傳《古文尚書》,皇甫謐採之作《世紀》,至梅賾奏上其書於朝,攷之《晉書》,並無此事。
《本紀》無文。
《儒林傳》中不載此事。蘇愉、梁柳、臧曹、梅賾亦皆無傳。《鄭沖傳》中但有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之語,並無所講乃孔氏五十八篇之文。
《皇甫謐傳》中但有梁柳爲太守,謐不爲加禮一事,竝無柳傳《古文尚書》及謐得之之文。
按:梅賾果當奏上此書,《本紀》即不之載,《儒林傳》中豈得竝無一言及之,乃非惟無其事,亦並無蘇愉等三人之名,然則三人亦皆子虛烏有者也。且凡紀事之體,必書年月,而《尚書正義》、《隋書》記此事,皆不言爲某帝之時,某年之事,蓋緣當時本無此事,繫之以時,則人覆檢而知其誣,故傳僞《書》者爲此含混之詞,使人無從辨其真僞,孔氏道聽途說,遂從而錄之耳。且夫五十八篇之《書》,魏以前未行於世也。當魏主講《尚書》之時,沖所執者果繫孔氏之五十八篇,《傳》豈得不大書特書,而乃但云《尚書》,即但云《尚書》,則即馬、鄭之二十九篇可知矣。柳爲太守,謐不加禮,瑣事耳,然猶載之《傳》中,若謐果從柳得《古文尚書》而作《帝王世紀》,此乃經術之顯晦,著作之本原,何得反略之而不記乎?嗟夫,《史記》、兩漢之書,人所共讀者也,乃明明與《今文》相校之《古文》,而謂之《今文》;明明別有百二篇,而謂之即二十四篇;明明壁藏其書者,而謂之口授;明明立學官,置弟子,而謂之私藏於家。彼其於共讀之《史》、《漢》尚不難以黑爲白,況人不多讀之《晉書》,亦何難以無爲有乎!
六駁之六:鄭、孔解詁與僞《書》之牴牾
一.非但梅賾未嘗奏上此書也,既鄭沖亦未嘗見此書,孔安國亦不知有此書,攷之《論語集解》可見。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政!”註:“包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友於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與爲政同。’”《論語集解》
按:《集解》乃鄭沖與何晏同纂輯者。所引包說,以“孝乎惟孝”爲句,以“施於有政”爲一家之政。今僞《書》此文無“孝乎”二字,而“施於有政”作“克施有政”,乃指治民之政而言,與包所說迥異。若沖果見此《書》,豈容復采包說!今何、鄭既以包訓爲是,則其未嘗見此《書》明矣。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注“孔曰:‘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論語集解》
按:今僞《書》此文乃湯滅夏之後告諸侯百姓者。安國果見此文,不當謂之“伐桀告天”。且今僞《書·湯誥》現有此文,安國何不注云“今《尚書·湯誥》有之”,乃反引《墨子》以爲證乎?安國既引墨子爲證,則是安國所見之《古文尚書》,竝無此文也明矣。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注:“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論語集解》
按此注,是以此言爲泛論周之事,以“周親”指周之公族,以“仁人”指商之賢臣也。今僞《書》此文乃武王誓師之詞,不惟管、蔡未叛,微、箕亦尚未來。安國果見此篇,何容復作此解!且僞《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反以周親屬商,以仁人屬周,與安國《論語》之注正相悖。然則僞《書》、僞《傳》之不出於安國明矣。
孔氏《正義》云:“此文與彼正同,而孔注與此異者,蓋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詞,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夫聖人之言一也,豈得忽以爲彼,忽以爲此。安國寧有此一口兩舌之事乎?此理顯然易見,而穎達猶欲曲全僞《傳》之說,抑亦異矣!嗟夫!安國西漢名儒,乃爲妄人所誣如是,爲穎達者不能爲乃祖辨其誣,顧反附會焯、炫而表章之,以致後儒摘斯《傳》之紕繆,動輒歸咎安國,使安國蒙不白之冤於千載之上,誰之過與!此餘之所爲長太息者也!
僞書之著者及其推行之年代
曰:五十八篇《經》、《傳》非孔安國所傳,梅賾所奏上,果何人所撰,至何時始行於世邪?曰:江左士大夫於經學皆不留意;罕有言及此者,此不可詳攷矣。但據其時所著之書觀之,王坦之東晉人也,范蔚宗宋元嘉時人也,藉令東晉之初此《書》果已奏上行世,坦之、蔚宗必無不見之者,而坦之著《廢莊論》,引“人心,道心”二語,不言其爲《虞書》(詳見《唐、虞攷信錄》中),是坦之未見此《書》也;蔚宗著《後漢書·儒林傳》,但云“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若不知別有二十五篇者,是蔚宗亦未見此《書》也。直至梁劉勰作《文心雕龍》,始引此二十五篇之文。然則是元嘉以前,此《書》初未嘗行於世,至齊、梁之際始出於江左也。然但行於江左已耳,中原猶未有此《書》。故《隋書·經籍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然則是隋滅陳以後,此《書》乃漸傳於北方,劉焯、劉炫之輩以爲奇貨而注釋之,然後此書大行而鄭注漸廢也。至其撰書之人,則梅鷟、李巨來皆以爲皇甫謐所作。以余觀之,不然。西晉之時,《今文》、《古文》並存於世,安能指《古文》爲《今文》,而別撰一《古文尚書》以欺當世?況謐果著此書,必已行世,何以蔚宗猶不之知,又何以江左盛行而中原反無之?然則此書乃南渡以後,晉、宋之間,宗王肅者之所僞撰,以駁鄭義而伸肅說者耳。何以言之?《左傳》“亂其紀綱”,舊說以爲夏桀之時,而肅以爲太康之世;《無逸》“其在祖甲”,馬、鄭以爲武丁之子,而肅以爲太甲之事。今僞《經》以“亂其紀綱”入《五子之歌》,僞《傳》以祖甲爲太甲,明明祖述肅說,暗攻先儒,其爲宗肅學者之所僞撰,毫無疑義。蓋漢末說經者皆宗康成,逮王肅起,恃其門閥,始好與鄭爲難。其說不無一二之勝於鄭,而荒唐悖謬者實多。但肅父爲魏三公,女爲晉太后,以故其徒遂盛,其說大行。天下之說經者分爲二派,一宗鄭學,一宗王學,宗鄭者黜王,宗王者駁鄭。適值永嘉之亂,《今文》失傳,江左學者目不之見,耳不之聞,又其時俊桀之材,非務清談,即殫心於詩賦筆劄,經術之士絕少,但見馬、鄭所傳與《今文》篇數同,遂誤以爲《今文》。由是宗肅學者得以僞撰此《書》以攻鄭氏。《書》既撰於晉、宋之間,故至齊、梁之際始行於當世也。孔氏但見僞《書》、僞《傳》之說多與肅同,不知其由,遂疑肅私見孔氏而秘之。夫肅專攻鄭氏,如果此《書》在前,肅嘗見之,其攻鄭氏之失,必引此《書》爲證,云《尚書》某篇云云,某《傳》云云,世人誰敢謂其說之不然,何爲但若出之於已然者?然則是僞《書》之采於肅說,非肅說之本於僞《書》明矣。即《正義》所稱“皇甫謐從梁柳得此《書》,故作《帝王世紀》,多載其語”者,亦作僞《書》者之采於《世紀》,正如《鶡冠子》采賈誼之《鵩鳥賦》,而人反謂誼賦之采於《鶡冠子》耳。但南北朝中無窮經博古之人察知其僞,遂使其《書》得行。然馬、鄭之本《書》尚在,後之人猶可攷而知之。至唐太宗時,孔穎達奉詔作《五經正義》,既不能辨其真僞,又誤以其《傳》真爲其祖安國所著,遂廢鄭注而用之,自是鄭氏古本遂亡,士人之應明經試者,莫不遵功令,讀僞《傳》,二十五篇之文遂與三十三篇之《經》並重,習而不察,以爲固然,竟不知《史》、《漢》以來,漢、晉諸儒所述並無此文,而出於後人之僞撰者矣。然不但今《尚書》二十五篇爲宗王肅者之所僞撰也,即今所傳《家語》亦肅之徒之所僞撰。《漢書·藝文志》云:“《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注云:“非今所有《家語》。”是今《家語》乃後人所僞撰,非漢所傳孔氏之《家語》也。今《家語》序云:“鄭氏學行五十載矣,自肅成童始志於學,而學鄭氏學矣,然尋文責實,攷其上下,義理不安,違錯者多,是以奪而易之。然世未明其款情,而謂其苟駁前師,以見異於人。”又云:“有孔猛者,家有其先人之書。昔相從學,頃還家,方取以來。與予所論,有若重規疊矩。”然則今之《家語》乃肅之徒所撰,以助肅而攻康成者,是以其文多與肅同而與鄭說互異。此序雖稱肅撰,亦未必果肅所自爲,疑亦其徒所作而讬名於肅者。由是言之,僞撰古書乃肅黨之長技,今僞《古文尚書》亦多與肅說同而與鄭氏異者,非肅黨爲之而誰爲之乎?
《孝經》之僞孔氏《經》、《傳》
亦不但《尚書》有僞孔氏古文《經》、《傳》也,即《孝經》亦有僞孔氏古文《經》、《傳》。《孝經正義》云:“隋開皇十四年,秘書學生王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王邵,以示河間劉炫。”則是後世所謂古文《孝經》者,出於隋世,非漢儒所傳孔壁之古文《孝經》也。又云:“開元七年,國子博士司馬貞議曰:‘今文《孝經》是漢河間王所得顔芝本。至劉向,以此參校古文,省除繁惑,定此一十八章。其古文二十二章,中朝遂亡其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傳學,假稱孔氏,輒穿鑿更改,又僞作《閨門》一章,以應二十二之數,非但《經》文不真,抑亦《傳》文淺僞。’由是明皇自注《孝經》,頒於天下,以十八章爲定。”則是南北分王之時,經術荒廢,好事者造爲僞書以惑當世,乃其常事也。但彼二十二章者,幸而有司馬貞駁其謬戾,以故不行於世,而此二十五篇者,不幸而遇孔穎達謬相推奉,黜真書而用僞者以取士,遂致唐人奉爲不刊之書耳。惜乎後世之儒之不能以三隅反也!
僞書破綻三端
曰:二十五篇之文果出後人所撰,何其似聖人之言也?曰:烏得似!後世學者不之察耳。三十三篇中,無一道學陳腐之語,然其所載行政用人之略及訓誥中所與其君及羣臣百姓言者,無一非修身經國之要務,不言道而道莫大焉,不言學而學莫純焉。其二十五篇則不然:自其所采《經》、《傳》舊文而外,大率皆道學語。然按之乃陳腐膚淺,亦有雜入於異端者。其義不逮,一也。三十三篇之中,事多於言,事亦皆與《經》、《傳》相應,無可議者。二十五篇則言多而事少,其事皆雜采於諸子及漢儒之注說,攷之於《經》既不合,揆之以理亦多謬。其事不經,二也。三十三篇,四代之書,迥然四代之文,古今升降,一望了然,《典》、《謨》、《誓》、《誥》各有其體,不相混也。二十五篇則自《大禹謨》至《冏命》,其文如出一手,《謨》、《訓》、《命》、《誥》約略相似,更無分別。其文不類,三也。昔宋阮逸僞造《元經》,稱隋王通所撰,而《河汾王氏書目》無之,《唐·藝文志》亦無之,且避唐景帝(神堯之祖)諱,稱石虎爲季龍,又避唐神堯諱,稱戴淵爲若思。以故直齋陳氏得知其僞,謂“逸心勞日拙,自不能掩”。今此二十五篇,《史記》無之,班、范兩漢之《書》無之,賈逵、馬融、鄭康成之所傳亦無之,趙岐、杜預、韋昭諸儒皆不之見,而其中雜以異端之言、小說之事,魏晉排偶組練之文,與三十三篇之《書》高下懸絕,較之阮逸僞書尤爲易辨。惜乎後世學者震於其名,而皆不之察也!
僞《書》剽竊《經》、《傳》
曰:《經》、《傳》所引《尚書》之文,二十五篇之中皆有之,何以言其僞也?曰:此作僞《書》者剽竊《經》、《傳》之文入其中耳。子不見夫鐵器乎,鑄者無痕而補者有痕。凡《經》、《傳》所引之語在三十三篇中者,與上下文義皆自然相屬;在二十五篇中者,其上下承接皆有補綴之跡,其有痕無痕至易辨也。且其中有《傳》、《記》所引《逸書》之文而剽竊之者,亦有《傳》、《記》之所自言,並非引《書》,而亦剽竊之者。“六府三事”,卻缺自解《經》文;“同德度義”,萇弘自抒己見,豈得牽帥之以入《經》!至於“除惡務本”,乃權謀之士所言,尤不得入聖人口中也。有采《經》、《傳》之意而改其詞者。“有攸不爲臣,東徵”,刪其首句而之伐紂,可乎?“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改以爲“予”而屬之武王,謬也!有采《經》、《傳》之詞而失其意者。周親之不如仁人,謂己不私其親,可也;以周親屬之紂,則不倫。嘉謀之歸於我后,臣下自相勉勵,可也;成王以之命官,則失言。此剽竊之不能掩者也。且《尚書》凡百篇,而凡《經》、《傳》所引略已盡於二十五篇之中,然則其餘四十二篇(五十八篇外,尚當有《逸書》四十二篇)《經》、《傳》遂無引其一語者乎?是以《傳記》所引在三十三篇中者少,在二十五篇中者多。何者?彼固專以裒集《傳記》之語成文者也。即以其引《傳記》觀之,而其僞已不能掩矣!
識別僞《書》之不易
曰:三代有三代之文,兩漢有兩漢之文,魏、晉以還,文體益變,二十五篇之文豈後世文人之所能贋爲?此固不得疑爲僞也。曰:能贋者多矣!魏、晉之世,文士多好摩擬古人之文,其習尚然也。若夏侯湛之《昆弟誥》,其聲音笑貌儼然《尚書》矣,試隱其名而加以古人之名,使無識之人觀之,豈復有疑其僞者乎!宋文彥博師永興,得褚遂良《聖教序》墨蹟,因令子弟臨摹一本,會宴僚屬,乃並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皆以摹者爲真跡也。夫書法,其淺者也,猶且如是,況文之難知乎?嗟夫,《管》、《晏》、《鶡冠》諸子,大率皆後人所僞撰,至於昭明所選《高唐》、《風賦》、《黃鵠怨歌》之屬,爲後人所擬作者尤多,乃傳之日久,而人遂莫不信以爲真。故凡世之以僞亂真者,惟實有學術而能文章者然後乃能辨之,悠悠世俗之目,其視莠莫非稷也,視魚目莫非珠也,烏乎其能知之?昔隋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劉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後有人訟之,坐除名。然則僞造古書乃昔人之常事,使不遇訟之者,則至今必奉爲聖人之言矣。古今之如此者,豈可勝道,特難爲不學而耳食者言耳。縱使梅賾果嘗奏上此《書》,尚不可據爲實,況並無此事乎!此所關於聖人之政事言行者非小,故余不辭尤謗而攷辨之。
卷之二
集前人論《尚書》真僞
二十五篇之僞,非述一人之私言也,古人固已有之。蓋唐儒疑而未言,宋儒言而未決,至南宋之末,趙氏始決言其僞。自是以後,言者益多。但世之學者咸篤志於舉業,不深攷耳。今略載其一二於左。
韓愈疑僞《書》
韓子《進平淮西碑表》云:“其載於《書》,則堯、舜二《典》,夏之《禹貢》,殷之《盤庚》、周之《五誥》。”《進學解》云:“《周誥》、《殷盤》,詰曲聱牙。”
按:於夏不稱《禹謨》而稱《禹貢》,於殷、周不稱《湯誥》、《武成》而反稱《盤庚》、《五誥》,則是其文淺陋平弱,韓子固已疑之,但未形於文耳。
朱熹疑僞《書》
《朱子語錄》云:“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來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因說《書》云:“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又云:“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按:朱子此語,則是明以二十五篇爲僞撰矣。惜其但及門人言之,未嘗自爲《書傳》,盡廢其僞而獨存其真也。
吳棫疑僞《書》
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爲隸古定,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
又論《泰誓》云:“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王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蔡沈疑僞《書》
九峰蔡氏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攷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所難,而安國攷定於科斗古書錯亂摩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
又《跋〈牧誓〉篇後》云:“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乎?”
按:吳、蔡兩先生所辨明矣,既以文體不同別之,復以義理有乖駁之,後學復何疑焉!惟口授之說原無其事,說已詳前卷《真僞源流通攷》中。
趙汝談疑僞《書》
陳直齊《書錄解題》云:“《南塘書說》三卷,趙汝談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決也。”
按:吳、蔡於此皆不能以無疑,然終未敢決言其僞。豈非久假難歸,極重難返,雖賢者亦不免遊移其間乎?乃趙氏獨直斥爲僞撰,非有大過人之識安能如是!惜余未得見其書也。近世以來,斥其僞者尤多。若梅、顧、朱、李諸先生,咸有論著。惜余學淺居僻,未見梅、朱二君之書,僅於李巨來《古文尚書》攷中見其一斑也。今載顧、李兩家之說於左:
顧炎武疑僞《書》
顧寧人論《泰誓》云:“商之德澤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紂,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曰‘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何至於此?紂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並其先世而讎之,豈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晉間人之僞撰者邪?吳氏、蔡氏蓋已見及乎此,特以注家之體,未敢直言其僞耳。”
李紱疑僞《書》
李巨來《古文尚書攷》云:“《古文尚書》,凡今文所無者,如出一手,蓋漢、魏人贋作。朱子亦嘗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帝王傳授心法,而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萬編修云:‘即此數言,可證其贋。危、微二語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經》,非《尚書》語也。梅鷟嘗言之矣。’余覆攷之,蓋《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爲李斯之師,其所著書在《詩》、《書》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詩》、《書》,並稱‘《詩》云’、‘《書》云’,而此獨稱‘《道經》曰’,則秦火之前荀子所見之《尚書》無‘危’‘微’語也。楊倞勉強遷就,注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者,蓋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從未嘗稱《易》、《詩》、《春秋》爲《經》,《論語》、《孟子》所引亦無‘經’字。且孔、孟爲儒家而黃、老爲道家,自戰國至漢無異辭。道家之書則曰《經》,如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列子《沖虛經》、關尹子《文始經》皆是。《道經》之非《尚書》也明矣。經解出於《戴記》,未必爲孔子之言,然通篇無‘經’字,其經目則漢儒所署耳。《孝經》亦漢人鈔撮聖賢緒言爲之,不然,不應漢以前無一人語及之也。至漢武帝始設五經博士。蓋漢初尚黃、老,儒者慕焉,因亦效道家者流,各尊其所治之書爲經,自稱曰經師。此如龐蘊《語錄》,惟僧人稱之,而宋儒弟子之無識者亦錄其師之言,名以《語錄》焉耳。其在秦以前,未聞稱《易》、《詩》、《書》、《春秋》爲經也。知‘危’‘微’之語出於《道經》而非出於《尚書》,然後知《古文尚書》之贋較然明白。或謂孔壁之書,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班固,漢人,其言不可據乎?曰:班說是也。然司馬遷所引者,安國所得於壁中之真《古文尚書》,非今所有之《古文尚書》也。秀水朱氏彜尊嘗攷之矣。《史記》中,《五帝本紀》引二《典》,《夏本紀》引《禹貢》、《臯陶謨》、《益稷》、《甘誓》,《殷本紀》引《湯誓》、《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周本紀》引《牧誓》、《甫刑》,《魯世家》引《金縢》、《無逸》、《費誓》,《燕世家》引《君奭》,《宋世家》引《微子》、《洪範》,皆今文《尚書》所有,不足爲據。其所引爲《古文》所有而《今文》所無者,惟《殷本紀》所引《湯誥》、《周本紀》所引《泰誓》二篇而已,然其辭皆與今所傳《古文尚書》絕不相類。蓋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書,而特非今世所行之《古文尚書》也。司馬遷親問故於安國,而所引之辭絕不類,則今之《古文尚書》復何所恃以取信於天下也哉?然則《尚書》之所謂可信者,皆其可疑者也。
按:百餘年以來,讀《書》有卓識者無過於顧寧人先生,所推爲博學者無過於李巨來先生,而皆以孔氏《經》、《傳》爲僞,則此二十五篇之非安國古文明矣。惟巨來稱“安國所得壁中古文信有其書,而特非今世所行之《古文尚書》”者,攷之尚有未详。蓋安國壁中之古文即今三十三篇之《書》,與《今文》篇數同而文字互異,前卷固已详言矣。司馬氏所引,班氏所稱,皆此也。此外十六篇,則所謂《尚書》逸篇者是也。但《今文》亡於永嘉,而人遂誤以三十三篇爲《今文》耳,非別有古文而今亡之也。故今補而正之。
李巨來《書〈古文尚書冤詞〉後》補說
毛西河有《古文尚書冤詞》,以二十五篇爲非僞(此書未見)。巨來作此辨之,深足以糾世人之惑。今摘錄之於此。然其中亦尚有未盡未周者,故復補其未備,附錄於後。
《晉書》無《古文》授受事
“余少時讀《尚書正義》攷《古文》授受引《晉書》云:‘晉太保鄭沖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攷之《晉書》,絕無其語,不知《正義》何所據也。按《晉書·鄭沖本傳》止云“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而已,竝未有古文之說。又稱沖與孫邑、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書,名曰《論語集解》,奏之魏朝,未聞有經學授之何人。又沖仕魏至司空司徒,常道鄉公即位,拜太保,位三司上,封壽光侯,而阿附司馬昭,比炎篡位,沖寶奉禪策,拜太傅,進爵爲公,視孔光、張禹之罪又有甚焉。此輩經術又安用哉?況蘇愉、臧曹、梅賾,《晉書》竝無其人,惟梁柳附見《皇甫謐傳》,亦止言其作郡,竝無得《古文尚書》之事。毛西河氏作《古文尚書冤詞》,亦據《正義》引《晉書·皇甫謐傳》云:“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中多載其語,則《謐傳》竝無之。毛氏乃引晁公武十八家《晉書》爲辭。按《唐書·藝文志》,唐初,《晉書》雖有七家,御製《晉書》矣。且御製《晉書》成於貞觀,而《唐書·儒學傳》謂《尚書正義》,永徽中於志寧等校正,始布天下,則《正義》自當引御製《晉書》,不當他引也。毛氏爲《古文尚書》稱冤,大聲疾呼,著書立說,而所引疎闊,與孔氏《正義》無異,安足以傳信後世而箝天下之口也哉!”
按:毛氏以十八家《晉書》爲解,不過強詞奪理而已。假使他《晉書》果有之,貞觀《晉書》必無刪之之理。聖經顯晦,天下之大事也,數百年亡軼之書一旦忽出,豈容略而不言!修《晉書》者與孔氏之書無仇也,何爲處處皆削其文?況當時方崇奉此書以爲真,乃無故削其文,尤不近於情理,然則是他《晉書》原無此語,故貞觀《晉書》亦不能鑿空而增此文也。此蓋傳僞《書》者假設此言以欺當世,孔氏道聽途說而未及覆核耳,不必曲爲之說也。毛氏乃欲以想當然之說定古《書》之真僞,謬矣!巨來此辨深足以正世人之惑,故今補而論之。
僞《書》與皇甫謐之關係
“攷晉時著書之富無若皇甫謐者,嘗因《正義》所引牽連梁柳,即疑《古文》爲謐所作。後得梅驚《尚書攷異》觀之,所見多相合者。其序文則直指《古文尚書》爲謐作以授梁柳。其別有所據耶?抑亦因《謐傳》及梁柳而臆揣之耶?‘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古文》之作自謐,可信十之六七矣。”
按:巨來以二十五篇爲僞,是也。惟從梅氏以爲皇甫謐作,尚恐未然。謐所著書雖多荒謬,然或採摘太雜,及附會以己意,則有之矣,若公然撰僞《經》以欺世,則謐尚未至是。且謐所著《帝王世紀》,湯之後有外丙、仲壬兩代,與《孟子》、《史記》合,而僞《傳》釋《伊訓》篇云:“湯崩,踰月太甲即位。”與謐說正相反,其非謐所著明甚。梅氏但因僞《書》、僞《傳》多采《世紀》之文,遂猜度之以爲謐作,誤矣。故今正之。
古書可贋造
“吾友方靈臯謂漢以來文章具在,就能贋爲之者。不知後人特未嘗摹《經》而自作文字,故不相似耳。劉原父嘗補作《禮經》三義,雜之《戴記》,有過之無不及,況搜集群書,徵引《尚書》原文,特以己意聊屬其間,因稍加補綴,何不似之有!黎邱鬼雖父不能辨其子,優孟爲叔敖衣冠,楚王不得不愛也。”
按:謂摹《經》所以似《經》,固也,然特其貌似,貌之一二分似耳,究之不脫當時風氣。試取其書讀之,文勢則多雜排偶,句法則率經煅煉,名言淺語間出錯陳,與三十三篇毫不相類,一望而知爲晉以後人之筆。以之欺世俗之人則有餘,以之入知文者之目,則固不能掩也。猶之乎蘇子瞻市豬於金華,中道而逸,買豬代之,而客猶贊其美,使其遇陸鴻漸,必不至以江水爲潭水也。
辨《晉書·荀崧傳》“《古文尚書》孔氏”語
又按:自漢下逮魏、晉,言《古文尚書》者衆口如一,無可以假借者。故毛、方兩家雖極力崇奉僞《書》,而皆毫無證據,其失不待言矣。惟唐貞觀中所纂《晉書》內二語,頗足惑世;然其誤亦顯然易見。毛、方雖皆未之及,然世人讀書粗心浮氣者多,恐數百年後復有以此獻疑者,故附辨之如左:
《晉書·荀崧傳》中記簡省博士事,內云:“《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似當晉時已有此僞《書》者。然按《傳》中所載,《春秋》、《左傳》二家,《易》、《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各一家,加以《尚書》二家,當爲博士十人,何以但云九人?前後不符,其爲誤衍孔氏一家無疑。且攷《職官志》,稱晉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江左減爲九人。魏既未嘗以孔《傳》列學官矣,晉安得而有之?而《隋書》亦稱齊建武中,孔《傳》始列國學。合觀諸書,孔氏之文之爲誤衍,不待問者。蓋今之《晉書》乃唐人采七家《晉書》而纂錄之者,鄭氏本傳《古文尚書》,是以舊《晉書》有《古文尚書》之文,而當唐初,人皆指僞孔氏《經》、《傳》爲古文,纂《晉書》者因誤以所稱《古文尚書》者爲孔氏僞《書》,遂於鄭氏之外別出孔氏之文,以致其數不相合耳。且《尚書》非古文則今文,非今文則古文,今乃云“《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然則鄭氏者今文邪?蓋隋、唐間學者專尚詞賦,不甚通於經術,而唐初承大亂之後,廷臣之有學問者少,故不敢定馬、鄭之爲古文、今文。謂爲今文,則永嘉之亂今文已亡;謂爲古文,則又別有五十八篇僞孔氏之《經》、《傳》與鄭互異,故不得已而爲是兩可騎牆之語耳。大抵古來自修之史多佳,詞臣共修者多不佳。自修者,必有其所見,其平日亦必详攷之,否則恐有舛誤,貽譏後世,故佳者多,《史記》、兩《漢》、南北《史》等書是也。詞臣共修之書,則多以官使之,未必皆有學術,其平日亦未當留心於此,而又不專其事,即有牴牾,莫適任咎,故佳者少。是以伏生之《書》本屬壁中所藏,而《隋書》稱“伏生口授二十八篇”;杜林本傳孔氏《古文尚書》,而《隋書》稱“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皆習於世俗流傳之語,而未當取《史》、《漢》諸書核正其是非耳。蓋凡古來詞臣共修之書多不可據如此,劉知幾《史通》言之詳矣。《隋書》、《晉書》皆唐初人所纂,復何怪乎《荀崧傳》中之誤衍此文也!
《堯典》分出《舜典》攷辨
今世所傳《尚書》,首有《堯典》、《舜典》兩篇,《堯典》自“曰若稽古”起,至“帝曰欽哉”止,《舜典》自“曰若稽古”起至“陟方乃死”止。習舉業者幼而讀之,以爲《古文尚書》果如是矣。不知此乃唐孔穎達所改之本,自隋以前,《尚書》原文本繫一篇,而無“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但學者皆爲舉業計,不攷之古,非惟不知孰爲古文,孰爲今文,甚至竝不知有古文、今文之名者,況能知《舜典》之爲後人所分乎?余於《唐、虞攷信錄》固已辨之。今因詳攷《古文尚書》真僞,復縷陳其本末是非如左:
伏生《堯典》
一.伏生所傳今文《尚書》,通爲《堯典》,竝不別分《舜典》。今文《尚書》凡二十八篇(篇目詳見《古文尚書源流真僞攷》中),首爲《堯典》,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帝曰欽哉”,即繼以“慎徽五典”云云,至“陟方乃死”止,不惟不分兩篇,亦無“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則是戰國西漢以來通爲《堯典》矣。
孔氏《舜典》篇
一.孔安國所傳《古文尚書》於二十八篇外,得多十六篇(篇目已見《古文真僞攷》中),內有《舜典》一篇。而《堯典》篇“帝曰欽哉”之下,仍繼以“慎徽五典”云云,至“陟方乃死”止。其十六篇學者罕所誦習,馬融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者也。其後鄭康成注《尚書》,分《盤庚》爲三篇,分《顧命》後章爲《康王之誥》,而《堯典》未嘗分。則是東漢、魏、晉以來,亦通爲《堯典》矣。
分《堯典》爲《舜典》之說
一.東晉以後,僞《古文尚書》出,於二十八篇外多《大禹謨》等二十五篇(篇目已見《古文真僞攷》中),分出《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四篇,而無《舜典》。或云《舜典》缺也,或云“慎徽五典”以下當爲《舜典》,自是始有分《堯典》爲《舜典》之說。然尚未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也。
十二字及十六字之出現
一.據《正義》稱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古文尚書》,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十二字,在“慎徽五典”之前。方興尋以他罪誅死,以故其書不行於世。或云“協於帝”下復有“睿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十六字。《正義》兩載其說,不能詳也。
二十八字之定爲《舜典》之首
一.隋開皇時購求遺書,有人稱得方興之二十八字者,因而漸行於世。及唐初,孔穎達作《尚書正義》,遂定以爲《舜典》之首,冠於“慎徽五典”之前。由是《堯典》一篇分以爲二。唐、宋學者不究其始,靡然從之。然以《經》文攷之,乖謬累累,顯然可見。故歴辨之如左:
割去《堯典》下文之不通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嶽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於嬀內,嬪於虞。帝曰:欽哉!
按:堯、舜之事既分二《典》,則堯之事皆當載之於《堯典》中。況自“師錫帝”以後,至“受終於文祖”,皆記堯舉舜之事,事相承,文相貫也。若至“帝曰欽哉”而止,非惟其事未畢,而其文亦未完,何得遽割其下文而屬之《舜典》,致文有首而無尾,而堯亦有始而無終。天下寧有如是不通之史官乎!然則“慎徽五典”以後仍當爲《堯典》,不得爲《舜典》,明矣。
堯讓位時稱帝
帝曰:格,汝舜!詢事攷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於德,弗嗣。
按:《堯典》首有“曰若稽古帝堯”,故其後皆以“帝”稱堯,而不斥言“堯”。今《舜典》首亦有“曰若稽古帝舜”,則其後文亦當以“帝”稱舜,而不斥言“舜”。今反稱堯爲帝而稱舜爲名,《經》、《傳》中有如是之文理邪?《春秋》於諸侯之事皆書某國,書其君爲某侯,獨於魯則書曰:“我”,於魯君則書曰“公”。何者?《春秋》,魯史也。若晉之《乘》,楚之《檮杌》,則必書晉、楚爲我,晉、楚之君爲公爲王,而書魯爲魯,魯君爲魯侯,明矣。豈有《舜典》中而以“帝”稱堯,而以“舜”稱“舜”者哉!然則此爲《堯典》中語而非《舜典》之文,明矣。
堯殂落時稱帝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攷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
按:堯至是始殂落,則以前之事皆屬之《堯典》。且既名爲《舜典》,篇首又有“曰若稽古帝舜”之文,所謂“帝乃殂落”者,堯乎?舜乎?史册如此,將何以傳信於後世乎!此乃君臣大義所關,非小小者可比,不知向來諸儒何以相沿而不覺也?前章稱舜以名,猶曰堯尚在也,今則堯已崩矣,何以猶稱舜而不稱爲帝?然則此篇之爲《堯典》而非《舜典》,明矣。
舜命九官時之稱謂
舜曰:咨,四嶽!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慰哉!
按:此後舜命九官之文皆稱舜爲帝。何者?堯已殂落,稱帝無所嫌也。然命官之首仍稱舜以冠之者,何居?蓋此篇,《堯典》也,故於舜必別白言之,然後其文始明。故此文之先冠以“舜曰”,猶《堯典》首之先冠以“曰若稽古帝堯”也。有“曰若”一語,則後文之稱帝皆堯矣,有“舜曰”之文,則後文之稱帝皆舜矣。古人之文謹嚴如此,而後人猶亂之,可傷也夫!前章稱舜,猶曰堯崩初也,此則堯崩久矣,何以仍冠以舜?然則此篇之爲《堯典》而《舜典》矣。
《堯典》篇終又稱舜名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按:前章命官之文既稱舜爲帝矣,此何以又別白而稱爲舜?堯之殂落稱爲帝,何以舜之陟獨稱爲舜也?且堯殂落之後,備言百姓四海哀慕之誠,舜之功德不亞於堯,何以絕無一言及之,而但追述其徵庸在位之年,意何居焉?蓋此篇,《堯典》也,舜即位後固當以帝稱之,若敘舜之始終,則必別白以舜稱之,始與文體相稱。且堯功德之隆惟在舉舜,故於篇終備記舜徵庸在位之年,以著舜終始,而後堯之功始全。若百姓四海之哀慕舜,固當於《舜典》中言之,不必載於《堯典》也。然則此篇之爲《堯典》而非《舜典》,明矣。
《孟子》引《堯典》文
然此兩篇之當爲一篇,不待細攷《經》文而後知也,《孟子》固言之矣。《萬章》篇云:“《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攷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今此文乃在《舜典》中。然則自戰國以前,孔門所傳之《尚書》固通爲《堯典》一篇,不分《舜典》矣。
梁武帝辨二十八字
即二十八字之僞,亦不必細攷《經》文而後知也,梁武帝固已斥之矣。武帝云:“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然則“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作字必非《舜典》之文,明矣。
隋、唐時人妄信僞《書》之故
曰:然則何以至隋、唐而分爲兩篇,而增此二十八字也?曰:魏、晉以後,南北分王,國尚戰爭,士競詩賦,罕有以經學爲事者,以故僞者得以亂真。至隋,天下歸於一,始欲振興文教,於是牛宏奏請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然經學之荒已久,朝廷諸臣無復有學識能辨真僞者。是以劉炫僞造古書《連山易》、《魯史記》等百有餘卷,朝廷莫敢以爲僞也,遂信之而賞之;其後爲人所訟,始知其僞,然後免死除名而黜其書。而僞古文《孝經》亦開皇十四年王邵等所傳播,當時亦皆以爲真也;逮唐,始有覺其僞者(事並見前卷《尚書真僞攷》中)。是知隋世士大夫信僞《書》,乃其常事。況此文僅二十八字,尤不足爲異矣。穎達原無學術,故妄取而載之。而唐時最重詩賦進士之科,輕視明經,应明經舉者,不過遵功令取科第而已,誰復知攷其本末者。至宋,沿習日久,益視以爲固然,雖大儒亦不復異議,遂使聖人之經爲後人所雜亂,良可惜也!良可歎也!
讀僞《古文尚書》黏簽標記(大名《崔邁德臯隨筆》)
余弟邁著有《古文尚書攷》及《訥庵筆談》。其駁孔氏《經》、《傳》之僞,較顧、李兩先生之說尤詳。但《筆談》已摘載於《攷信錄》中,而《尚書攷》中所徵之書,所持之論,則余《源流真僞通攷》中已悉備之,不必復述。此外復有於爲《尚書》各篇中簽出字句所本,及剿襲而失其意,與措語之不當者,雖若細碎,然皆足資攷證。不忍盡棄,因復附錄於此。
辨僞古文《虞書》
《大禹謨》
“舍己從人”,語自《孟子》來。
“帝德廣連”,語本《呂覽》。
《左傳·文七年》,郤缺引《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壊!”
《僖二十四年》《傳》文引《夏書》曰:“地平天成。”
《莊八年》莊公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
《襄二十一年》臧武仲引《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哀六年》孔子引《夏書》曰:“允出茲在茲。”《襄二十三年》孔子引《夏書》曰:“念茲在茲。”
《襄二十六年》聲子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帝曰來禹”章,《論語》載堯命之語,而此乃抄襲之,卻又分作三處,用他語增飾之,謂人盡可欺也。《論語》此數句本繫韻語,今離而爲三,使有韻者無韻。
“洚水警予”,語本《孟子》。
《左傳·襄五年》引《夏書》曰:“成允成功。”
《周語》內史過引《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後非衆,無與守邦。”《左傳·哀十八年》引《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
“正月朔旦”一節,按《舜典》云“受終於文祖”,又云“舜格於文祖”,未有言受命者。命者,生人之事也。神宗既爲堯,則禹是時安得受命於堯乎?
“帝初於歴山”以下,語本《孟子》,而故改易之。
辨僞古文《夏書》
《五子之歌》
《周語》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晉語》知伯國引《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左傳·成十六年》單子引《夏書》曰:“怨豈在是,不見是圖。”
《左傳·哀六年》孔子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翼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胤徵》
《左傳·襄二十一年》祁奚引《書》曰:“聖有謨動,明徵定保。”
《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本《周禮·天官·小宰》。
《左傳·昭十七年》大史引《夏書》曰:“辰不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二十三年》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
《昭十四年》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賦殺。’臯陶之刑也。”
辨僞古文《商書》
《仲虺之浩》
“惟有慚德”,語本《左傳》季札語。
《左傳·昭二十八年》晉叔游云:“《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
晉人尚排偶,故二十五篇中多偶語,如“苗之有莠”及“不邇聲色”、“德懋懋官”等語皆是。三十三篇中亦間有偶語,要有多少自然氣象,即比體亦不若“苗之有莠”語氣稚弱也。
“葛伯仇餉”一節,語本《孟子》,而增減改易之。
《左傳·襄十四年》中行獻子引“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宣十二年》士會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襄三十年》子皮引仲虺之志,亦四句,“亡者”句在下,“道”作“利”。
《湯誥》
《周語》單襄公引“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邦,無從非彜,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未嘗言《書》也。此分作二處用。
《論語》載《湯誥》一節,此則離合增減而用之。“簡在帝心”,承上“帝臣不蔽”而云“有罪不敢赦”,言人之有罪,湯不敢赦也,此作“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失其義矣。《周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事,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餘一人。”
《伊訓》
“百官總己以聽塚宰”,語本《論語》。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語本《孟子》“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學《禮記》語。
“爾惟德,罔小”數語,即昭烈“勿以善小而不爲”二句語意。此貪作參差對待語,而其實一意。乃曰“罔小”,曰“罔天”,遂令下句不可解。
《太甲上》
“顧諟天之明命”,本《大學》。
“昧爽丕顯”,本《左傳》讒鼎之銘。
“坐以待旦”,用《孟子》語。
“予弗狎於弗順”,本《孟子》。
《太甲中》
《左傳·昭十年》鄭子皮引《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語本《孟子》。
“徯我后,后來無罰”,語本《孟子》。《孟子》所言本一語,而兩地異耳;此遂作兩處,而不知《孟子》所引上段固同也。
《太甲下》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語自《左傳》來。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語學《中庸》。
《禮記·文王世子》引《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咸有一德》
“天難諶,命靡常”,上句《詩·大明》篇語,下句《詩·文王》篇語。“天難諶”,《書·君奭》篇語。
《說命上》
《楚語》白公子張謂楚王曰:“昔殷武丁能從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命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津水,用汝作舟。若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樂不暝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稟令,皆自上而下之詞。《國語》言“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言不出命令也。此改作“臣下罔攸稟令”,便不通矣。“若樂不暝”二句,又見《孟子》。
《無逸》言“其惟不言,言乃雍”,猶言不言則已,言必和也;此截去下句而止用“其惟不言”,不知其不成文理也。《禮·檀弓》子張引《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論語》、《禮記·喪服》篇皆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而此則變其語。
《左傳·昭六年》叔向引《書》曰:“聖作則。”
“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語亦本白公。
《說命中》
《左傳·襄十一年》魏絳引“《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杜注止上一句爲《逸書》。
《定元年》士伯曰:“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
《說命下》
“入宅於河,自河徂亳”,語本《國語》白公。
“爾交修予,罔予葉”,語本《國語》白公。
《學記》引《兌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又引《兌命》曰:“學,學半。”
《禮記·文王世子》引《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學記》引《兌命》,同。
辨僞古文《周書》
《泰誓上》
晉人詩文發端,多從遠處說起。如此篇“惟天地萬物父母”等語,及《仲虺之浩》“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湯浩》“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之類,皆迂遠,正是晉人氣習。試讀《甘誓》、《湯誓》、《牧誓》,有此等語否?
數紂之罪,皆以後世之事想像彙集而成。無論紂之罪不若是之甚,而武王亦必不肯作此毫無含蓄之語。至“以殘害於爾萬姓”句,尤疎謬。凡誓者,皆誓己之衆也,首呼“友邦塚君,御事庶士”而誓之,則所謂“爾萬姓”者,何人也耶?
族人者,秦之法,三代未有也。“罪人以族”之語,謬矣。
“弗事上帝神祗,遺厥先宗廟弗祀”,語本《牧誓》“昏棄厥肆祀弗答”。“犧牲粢盛,既於凶盜”,語本《微子》“今殷民乃攘竊神祗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天佑下民”至“越厥志”,語本《孟子》而有改易。
“同德度義”,語本《左傳·昭二十四年》萇弘語。
“貫盈”二字,本《左傳》“使疾其民,以盈其貫”語。此後世四六剪綴字句之學也。
“類於上帝,宜於塚土”,本《王制》“天子出徵,類乎上帝,宜乎社”之語。
《鄭語》引《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周語》亦引之。《左傳·襄三十一年》穆叔引《太誓》二句。《昭元年》子羽亦引之。
《泰誓中》
“播棄黎老”,學《國語》子晉語。
“謂己有天命”,本《西伯戡黎》“我生不有命在天”。
“厥鑒惟不遠”二句,本《詩》“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周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於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
《左傳·昭二十四年》萇弘曰:“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文引“《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予有亂臣”句,又本《論語》。
“雖有周親”二句,本《論語》。
“天視”二句,本《孟子》。
“百姓有過”二句,本《孟子》。
“我武惟揚”五句,本《孟子》。
“罔或無畏”數句,本《孟子》而改易之。“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此武王伐商告諭商民之語,言汝無畏懼,乃來安集汝,非與汝爲敵也。而百姓由是咸悦歡呼,稽顙雷動,故曰“若崩厥角稽首”。此改“無畏”曰“罔或無畏”,“非敵”曰“寧執非敵”,語既晦澀難解,又以爲誓師之語,全失武王伐罪惡弔民之意。而“百姓”字又與“非敵”截斷;“若崩厥角”又以爲武王口中語。“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語更不可解。注以爲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其頭角,此與上下何所干涉?《孟子》所記本明白正大,作《書》者必欲掩其抄取之跡,改易不通,真令人欲笑欲罵。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語意本《漢書》引《泰誓》。《漢書》引《泰誓》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
《泰誓下》
“剖賢人之心”,語自《史記》來。
“恭行天罰”,語自《牧誓》來。
“獨夫紂”,本《孟子》“聞誅一夫紂矣”。
“犬馬,寇讎”,孟子爲齊宣王言之也,後世猶以爲譏。《泰誓》乃曰:“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無論文王怙冒西土,不至苦紂之虐,即使苦紂之虐,而武王亦必不忍爲此言。姦雄篡竊之輩雖殘忍刻薄,而良心未能盡喪,亦不能不慚恧於其際。況武王以聖人處人倫之變,而乃公然告諭其下,與之殄殲乃讎,此乃天下之亂首而病狂喪心者之言也,豈可以污武王哉!
《左傳·哀元年》伍員言“樹德莫如滋”。
“迪果毅”,語本《左傳》。
《武成》
“歸馬”二句,本《樂記》。《樂記》:“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此去“弗復乘”句,不知服牛乘馬非通用也。
《左傳·襄三十一年》北宮文子引《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
《左傳·昭七年》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肆予東徵”數句,本《孟子》而改易之。
“惟爾有神”,“無作神羞”,語俱自《左傳》來。
“受率其旅若林”,語自《詩經》來。
“血流漂杵”,語本《孟子》。
“一戎衣”句,語自《中庸》來。
“大賚”句,自《論語》來。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自《論語》“所重民食喪祭”來。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語本《魯語·仲尼在陳》篇。
“王乃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四句,語本《魯語》“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及“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語本《左傳》。
“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語意本《論語》。
以下諸篇並缺。
跋
右《尚書辨僞》二卷,先生晚年作,而卓識早定,故前著《攷信錄》絕不稱引一語,且力駁之。自宋、元以來,論辨《尚書》者何啻數十家。前明梅氏、國朝閻氏洋洋大篇,先生皆未之見。由今觀之,正不啻數百年間人同堂講晰。先生識力所至,闇與古合,更有發前人所未發者。履和藏先生全書久,昔年在都,質之尚書山陽汪公,公悦之序之。既出都,又聞有宜興任君泰,悦其書,作詩歎賞,以爲“大谨乃如狂,至允反不平”,令人一讀一起舞。嗟乎,是何可多得!而履和既不能長侍汪公,執弟子之儀,又不獲一見任君,悉其生平何如,爲可惜也。僞《書》二十五篇,人人童而習之,昔賢辨論尚未必首肯,何況晚出之作,衆難群疑,固然不足怪。伏思我朝《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一書,皆奉高宗純皇帝欽定,刊佈海內,古文二十五篇之僞,朝廷早有定論,非草茅下士一人一家之私言也,故今刻《辨僞》一書,恭錄《提要》中論《尚書》三則,別爲一册,以冠篇首,俾閱《辨僞》者先敬觀此三則,庶胸中目下如離照當中,群陰開霽,從此縱覽諸家,大有破竹之樂矣。
道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履和谨跋
斌大 辛苦了!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