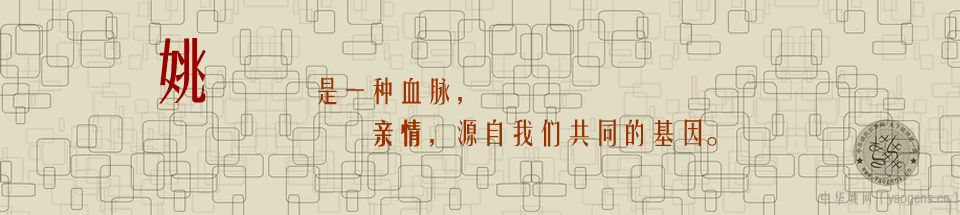舜与韶乐及与东夷文化关系浅议
舜与韶乐及与东夷文化关系浅议 崔永胜 在古代,音乐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宗教和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音乐可以使各阶层的人心灵彼此沟通,化解因身份差别而形成的隔阂,产生和谐的情感。故《国语·周语下》认为乐乃“和之道也”。《礼记·乐记》曰:“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因此,一个古代部族的音乐发展水平体现了部族中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程度和向心力的强弱,并且从很大程度上代表着这一部族的文化水平和社会调节能力的高低。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发掘和学界研究的深入,东夷集团生活的中心区域——海岱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已成为大家的共识。不仅如此,东夷集团还是一个礼乐文化相当发达的部族。礼器方面的实物资料,如诸城呈子、潍城姚官庄、日照两城镇等遗址出土的“薄如纸,明如镜,黑如漆”的蛋壳陶,代表着古代人类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以及具有东夷特色的口部被拉长尖到夸张程度的陶鬶,经考证非日常实用器,而很可能是用于祭祀的礼器。作为与原始祭祀活动相伴相生的音乐实物,有青州桃园遗址出土的陶鼓、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的陶号和笛柄杯、胶南西寺村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响器,潍坊姚官庄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无论从质量、种类,还是从集中程度来看,作为东夷文化发源地和中心的潍坊地区的音乐发展水平都应高于同时期其他地区。《竹书纪年》中有夏时“诸夷入舞”、“献其乐舞”的记载,因此在夏前后,东夷集团还保留有较高的礼乐文化。作为一个有音乐传统的东夷部族的首领,出生在山东诸城诸冯的舜与音乐结下了很深的缘分。舜之部族首领世代为“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通过乐律来预测春天的到来,以准时组织原始农业生产。可见是后世之专门执掌音乐以观风俗的“太师”、“少师”一类乐官。古籍中记载舜及其父瞽叟发明或改进的乐器有箫、瑟等。更重要的是作为后世历代宫廷大乐的《韶》乐也为舜所创。因此专家认为,舜之部族精通音乐并非个别现象,而应是整个族群共同的技能特长,并且在乐器、乐律、乐曲创作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首先我们看一下《史记·五帝本纪》中舜的世系:昌意——颛顼——穷蝉——敬康——句望——桥牛——瞽瞍——重华。其中瞽瞍之祖句望又写作“句芒”,《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三月:远古时期“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山海经·海外东经》:“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按五行的说法,东方属木,其形象也与以鸟为图腾的东夷集团相符,可见句芒必然是东方的方伯。另外,《国语·郑语》曰:“虞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虞慕为舜之部落有虞氏之先祖,据卜辞及《山海经》,协风为东方之风,虞慕为司东方之风的官员。联系以上句芒为管理东方的方伯,有虞氏与东方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与有虞氏地望有关。关于舜父瞽瞍,清人汪中《述学》补遗《瞽瞍说》考证“瞽瞍”应为乐官官名,《史记》中误会为“瞎老头”实属荒谬。舜之父即为尧时乐官,且在尧乐《大章》的创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他对瑟的改造也就不足为奇了。有虞氏世代精通乐律,并有多人担任乐官,在远古各部族专司一职和世官世职的背景下,乐官当为舜部族代代传承之世职。经过世代的积淀,这一音乐部族的艺术天才在《韶》乐的创作中得到完美体现。作为有着悠久音乐积淀部族首领的舜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欲以乐传教于天下”(《吕氏春秋·察传》),因此也就有了《韶》乐的创作。《韶》又称《招》、《九韶》、《九招》、《大韶》、《韶箾》、《箫韶》、《韶虞》,为舜所创,古籍所载几乎众口一词。《韶》乐演奏的最早记载见《尚书·益稷》中舜让乐官夔演奏的情景: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后德让。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记载虽短,但其中蕴涵的信息极为丰富。其中涉及《韶》乐演奏所用的各种乐器“鸣球”、“搏拊”、“琴”、“瑟”、“管”、“鞀鼓”、“柷敔”、“笙”、“镛”;演奏《韶》乐的场合,所谓“祖考来格”,可见与祭祀活动有关,“鸟兽跄跄”指以各种鸟兽为图腾的部族首领们随着《韶》乐起舞朝拜,可见与部族联盟会议有关,而最终的“凤凰来仪”则突出了以凤鸟为图腾的东夷部族的联盟首领地位。同时,作为《韶》乐中主要乐器的箫也为东夷人所创。关于箫的形制,《世本·作篇》(茆泮林辑本)记载:“箫,舜所造,其形参差象凤翼,十管,长二尺。”可见,箫的形制应与现代的排箫相似,而上古时期单管吹奏的乐器,不管横吹还是竖吹,都称为笛。排箫形状仿造飞鸟的翅膀,可能与东夷族对飞鸟的图腾崇拜有关。但竹制乐器极易腐朽,因此至今还没有实物证据。有人认为在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大汶口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墓葬中陶尊上的三个相似的陶文应为东夷先民对竹制竖吹管乐器的祖型的描画,如果此说成立,亦可佐证箫为东夷人所发明,进一步从考古学上证明东夷部族音乐文化的发展水平。舜以后《韶》乐的传承嬗变,姜亮夫先生认为:“《韶》者,夏以为歌舞节奏之主乐,因以为歌舞之号……自后启曾修之,至商汤又修之,周备六代之乐,《韶》舞不废。春秋之兴,周室衰微,而乐散在诸国,鲁、齐、陈、杞皆传习之。”四国传承之《韶》乐的具体情况又有不同:鲁为周公封国,所封之处亦为东夷故地,周公子伯禽之国后,用三年的时间,“变其俗,革其礼”,东夷文化在鲁国遭到毁灭性破坏。同时作为对周公大功的奖赏,鲁国得到了高于其他诸侯国的礼乐制度,所谓“备四代之乐”,其中就包括有虞氏之乐。可见,鲁《韶》应是中央颁赐、经过周文化改造的“舶来品”。杞为有夏故国,其《韶》乐最早当是夏启改造过的《韶》而非原始《韶》乐。进一步说,商周以来杞国或封或废,迁徙不常,周初分封之地也与其故国相去甚远,作为周朝“兴灭国,继绝世”的摆设,杞国名为故国,实为新封,所以杞国的《韶》乐很可能与鲁国的情况相同,得自周室颁赐。陈国作为虞舜正裔,后代虽颠沛流离,对先世礼乐尚能抱残守缺,或还保有虞舜时期的部分礼乐,作为大乐的《韶》当在其中。齐桓公十四年(前672年,陈宣公十一年),陈宣公杀太子御寇,陈国公子陈完与御寇相友爱,恐祸连己,遂奔于齐,因此陈《韶》在这时可能人于齐,其优点并为齐《韶》所吸取,大大提高了齐《韶》的演奏水平。齐《韶》的情况不同,齐太公到齐国后,与山东半岛的土著居民,也是古东夷族留在祖居地的后裔——莱夷发生激烈冲突,“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莱夷在当时已经形成了高度发达又有别于其他部族的民俗文化传统,要不也不存在“因”、“简”的问题,周文化的侵入使两种文化的冲突在所难免。在冲突中,代表周文化的齐国并不处于绝对优势。因此,齐国国君灵活制定统治政策,承认夷、周东西文化的差异性,在用武力镇压的同时,对东夷人的文化传统给予充分尊重,很快稳定了统治秩序,也使东夷文化包括礼乐制度继续发展并逐渐与周文化融合,从而形成了以夷俗为主、以周俗为辅,以开放兼容为特色的齐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东夷的传统音乐《韶》得到了保留并继续完善发展。《韶》乐在春秋后的声名卓著主要缘于孔子: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尔》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眼中,春秋时期鲁国的礼乐制度总体水平远在齐国之上,“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种对齐地《韶》乐的赞扬不能不让人心生疑窦。孔子在齐国闻《韶》是在公元前517年前后,而季札在鲁国欣赏到《韶》乐是在公元前544年,短短二十几年时间,《韶》乐不可能在鲁国绝迹,使孔子不得不跑到齐国去赞赏《韶》乐。以孔子对古代礼乐的痴迷不可能没有听过鲁国的《韶》乐演奏,为什么单单齐国的《韶》乐演奏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顾颉刚认为,孔子在齐所闻之《韶》“为春秋时新声”,目孔子为爱听流行歌曲的“追星族”,未免“疑古”过勇。《礼记·乐记》中子夏与魏文侯论齐、宋、郑、卫四国“新乐”“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顾先生的说法过低估计了孔子的音乐鉴赏水平。因此,《韶》“为春秋之新声”的说法很难站得住脚。最合理的解释是,孔子在鲁国也听过《韶》,但是鲁国《韶》乐的演奏水平远远没有作为《韶》乐产生地——齐国的演奏水平高。为什么齐国《韶》乐的演奏水平超过其他地区呢?音乐地理学的理论认为,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及其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形成的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离开特定的文化现场,音乐的功能也就不复存在。这种某一地域的自然环境对当地文化的影响在交通相对闭塞的古代表现得更加明显,所谓“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诗经》风谣以地域分类以观风俗正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齐国高水平的《韶》乐演奏,基于齐国作为东夷故地和对当地东夷文化的充分保留和继承。齐太公立国之初,“因其俗,简其礼”,齐国文化继承了齐地以往的优秀文化传统,音乐也不例外。因此《礼记·乐记》师乙论乐,说:“齐之乐,三代之遗声也”。不仅如此,甚至齐国音乐中还保留了三代之前东夷古乐的因素,经过长期融合,这些因素已被包纳到当时的正声雅乐当中。同时,随着东夷部族的不断南迁,《韶》乐传向了楚、越等地。南迁东夷后裔对祖居地的文化尤其是与祖先崇拜有关的文化崇敬有加,如《水经注·湘水》:“(南岳岣嵝)山下有舜庙,南有祝融冢,楚灵王之世,山崩,毁其坟,得营丘九头图。”据考证,此“营丘九头图”即是昌乐崇山东夷远古石祖祭祀场景的再现。同样,楚人作为南迁东夷后裔,对主要用于祖先祭祀的《韶》乐充满特殊感情,也是这种情结的反映,周时楚地流行之《九歌》即为《韶》乐之变奏。楚、越一带多有以“韶”名地者,如湖南有韶山,《清一统志》:“相传舜南巡时奏《韶》乐于此,因名。”江西也有韶山,山侧有舜祠。广东古有韶石、韶州,今有韶关。如此多的与《韶》有关的地名,以至有南方学者反客为主,直认为《韶》为苗蛮文化的产物而反哺于中原文化者。秦朝后《韶》的传承,《隋书·何妥传》:“秦始皇灭齐,得齐《韶》乐;汉高祖灭秦,《韶》传于汉,高祖改名《文始》。”干脆不言周《韶》、鲁《韶》,而直以齐《韶》传之秦汉。秦汉后社会情势的重大变化使礼乐制度的内涵发生了变化,《韶》乐也在历代中央政府的不断改造中失去了原有的东夷文化特征和内涵。综上所述,东夷部族是我国古代礼乐文化尤其是音乐文化相当发达的族群,《韶》乐为舜在东夷乐舞基础上所创作,凝结了东夷部族世代的音乐文化积累,并体现了东夷族在史前先进的礼乐文化。春秋时期,《韶》乐在东夷族祖居地齐国开出最绚丽的花朵,在中国音乐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崔永胜:《舜与韶乐及与东夷文化关系浅议》,《诸城大舜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