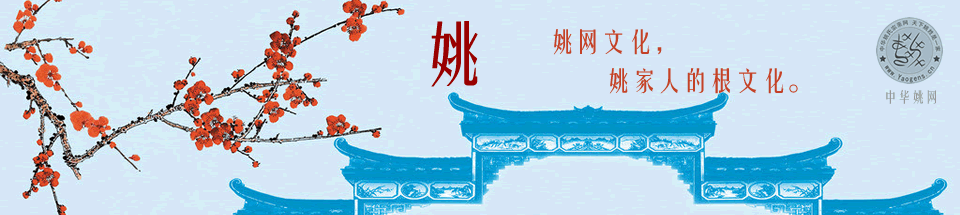抗战老兵姚福卿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f311d30100z73x.html一,抗战八年只留下一篇回忆录的抗战老兵抗战老兵姚福卿和女儿及其外孙一家四代人先练习一下砍头的日本鬼子姚福卿1921年出生,今年90岁。1936年,当学生的姚福卿就会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1937年姚福卿参加国军第13军抗日,是在汤恩伯的部队。他由于不愿意参加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所以,在1947年,他就离开国军了。1958年,在福建行医的姚福卿被浙江永康去的警察戴上手铐。押回原籍,判,基本上把他的人生分成两个部分:抗日战争时期:他是挺着腰板走路的人;抗战八年当中,他始终是光彩的人物。解放以后,他基本上是“夹着处徒刑。我和姚福卿聊天尾巴做人”、“逆来顺受”的过程。当然这种人生的心路历程的人屡见不鲜;我采访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物。歌颂国民党抗战将士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当政者至今也没有把他们列入“正面人物”行列。甚至,个别辱骂国民党抗战将士的仍然是自持是英雄的行为。更有甚者,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国民党反动派腐败的罪责仍然要普通士兵来承担。都梁是我的朋友和师长,春节见面,他说:“你写作的题材也换换?”我对我的愚钝很是难为情。但是,我清楚,我应该是最后一位热心采访、描写他们心路历程的人了吧?我可能是最后一位为他们写书的人吧?扪心自问,我还能坚持多少天呢? 当然,还会有很多人关心、爱护他们。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有朋友在我的博客留言,说:“我40岁了,完全没有对残渣余孽的印象。”我很同意这位朋友的话。基本上,50岁以下的人基本上不了解“地富反坏右份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所遭受到的待遇了。其实,说起他们的所谓“待遇”,写《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的著名作家老舍先生,就是个活生生例子。著名作家老舍能自己走到太平湖中去,那时,是一个什么年代呢?文革开始的时候害死了伟大的老舍先生。1966年夏天,“文革”风暴呼啸而至,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顷刻间陷入一场空前浩劫。文革中,同许多老一辈爱国文艺家一样,老舍遭到了恶毒攻击和迫害。1966年,他被逼无奈,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终年67岁。1966年8月23日,老舍去北京文联“参加运动”,受到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批斗。他们将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到老舍头上,使老舍遭到了人格上的侮辱。如此不堪忍受的侮辱降临到头上,老舍毫不犹豫,平静而坚定地选择了死亡。8月24日凌晨,年近古稀遍体鳞伤的老舍先生独自走出了生活了16年的百花小院,来到德胜门外城西北角上的太平湖,在太平湖边坐了整整一天和大半个夜晚,然后步入湖水自尽。没有人知道,在老舍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坐在太平湖边都想了些什么。其实,老舍先生所受到的困惑、侮辱,姚福卿老人都受过。有人会说,一个国军抗战老兵,他能和著名作家相比较吗?回答是:能!“地富反坏右、残渣余孽”就包括他们。姚福卿1937年就参加抗战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只在永康黄埔军校同学会所发表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而这些人都是抗战时期黄埔军校的学生,是二战时期世界四大军事名校的大学生。抗战八年,身经百战。他只写一篇回忆录,实在可惜。从这篇文章,我们像窥一斑而知全豹一样,看到抗战时期朝气蓬勃的姚福卿。姚福卿这一代人,就此,完结了。他们坎坷一生,一言难尽。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他们意气风发、豪情满怀;打败日本鬼子了,他们倒被入狱、受管制。他们是社会、时代、党派斗争、旧时代、旧观念的牺牲品。 妄图把中国打烂、把中国人打服气的日本鬼子日本鬼子的坦克部队、步兵在行进中抗击日寇,总会有伤亡。中国政府军在抗日战争时期牺牲321万军人;伤者无数。我问过姚福卿他的腰是怎么变成这样的?是不是抗战时期受伤?姚福卿矢口否认。潼 关 大 捷 姚福卿1944年5月,日侵略军从洛阳调来800辆坦克,一齐扑向潼关,实现队(区队长姚福卿),第三区队(区队长杨天作),共200余黄埔学生军负责专打日本坦克车的作战任务,配合我陆军主力保卫潼关。杨中队长其夺取潼关,乘势占领西安的战略野心。敌人的行动计划被我军情报部门截获,我国政府紧急告知驻我国的美国盟友马歇尔特使。马电告美国政府,总统罗斯福,当即向我方空运来专击坦克的新式武器火箭筒200支到西安黄埔军校。
校部决定派第三中队中队长杨荣率第一区队(区队长谷元鸥),第二区召集三个区队的师生们开会,做战前思想动员,同学们个个争先恐后地表决心,同学们在表决心时纷纷说:“为保国土,上刀山下火海,抗强敌流血牺牲在所不惜,誓保潼关不失守!”战前政治思想动员会议结束,全中队师生进入火箭筒的瞄准、射击操作的训练,掌握新式武器使用的技能技术,力求攻击能百发百中,歼灭敌人的坦克车。经过2小时的战前准备后,我们斗志昂扬地向潼关进发。到达战地之后,为打有把握的仗,中队长率三个区队长进入前沿阵地,详细地观察地形地物后,经四个指挥员精密的研究后,立即部署挖掘简单的防御掩体,以及火箭筒前后交叉火网的配置,我们的作战部署是把敌人的坦克分成三段打,第三区队负责打先头坦克,第二区队负责打中,第一区队负责打尾。既有各自的攻战目标,又互相配合,协调作战,中队长又交待我们要运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随机应变,沉着应战”的战术,把在课堂中学到的军事知识,在实战中检验。布局已定,任务到人。我们潜伏于阵地掩体中伺机杀敌。
不久日军坦克成群结队,耀武扬威向我火网驶来,待敌坦克全部钻进我火网圈中之后,中队长下令“打!”顷刻间,前、中、后的火箭一齐发射,无数的火箭钻进敌人坦克内,轰轰地爆炸、燃烧,天空中立刻腾起熊熊的烈火和滚滚的烟雾,只见敌人一辆辆昔时耀武扬威的宠然大物,若一头死兽般一动不动地横七竖八地躺卧在潼关前的阵地上,大大地挫伤了日军的元气,凯旋回校,学校举行庆功大会,校部给我们记功表彰。
作者:姚福卿,生于1921年,永康象珠镇郎下人,黄埔军校18期毕业,曾任黄埔军校中尉区队长。 二,我希望回到监狱和劳改农场生活姚福卿说:文革十年中我只希望回到监狱中生活,那里面不打人。采访开始,小楼是翻译。后面的房子是姚福卿爷爷的爷爷建的,已经230多年了。
采访姚福卿,给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印象,是他从田地里走回来。那是我们大家的初次见面。只见老远的,走过来一个老人,弯着腰,直不起来,步履有些蹒跚。
他一脸的沧桑、苦相。没有受过大灾大难的人,绝对不会被历史的刻刀在脸上雕刻上如此的形象的。
初次见面,我问他,您的腰,直不起来。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前线受的伤吗?
他苦笑着,不愿意回答。我想,这是不是他内心最为伤痛的故事呢?
90岁的姚福卿直了直已经直不起来的腰板,说:“抗战八年,我风流倜傥、意气风发、朝气蓬勃、充满青春活力。那时,我1 .7米身高。和侵华日军作战数十次。”
现在,姚福卿用站不直的身体站直的话,身高有1.47米。
姚福卿说,1936年,还在上中学的我,就参加了三青团。那时,国民党、三青团都宣传抗日思想。我和村里好几个同伴一起走到河南,找抗战的队伍。当时,13军有个师长是我们浙江金华人,叫周斌,是黄埔6期的。所以,我们去找他。
1937年,我在河南省,国军13军汤恩伯将军的部队入伍。同年,我在军队考入黄埔军校18期步兵科。我们在西安王曲总校学习。胡宗南是主任,教育长是汪耀煌,副主任是邱清泉。我们虽然是步科,但是,也学习迫击炮、高射炮,我们的训练科目中有:重兵器训练班。通过两年的学习,同学们被迅速补充到一线部队参加对日作战。
我继续留校任教,当区队长。中尉军衔。
潼关战役以后,我们部队调防河南洛阳,我升为上尉连长。我们团长是四川人,叫杨教南。抗战胜利以后,部队整编,我被编入无锡17军官总队。那时,我的军衔已经是少校了。当时,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军官都被退役了。
1947年,人心不安定。内战四起。那时,我就请长假回家了。
1947年的中国铁路,国军军官坐火车是不要钱的。所以,我常常穿上呢子军装坐“上海到福州”的线路,倒腾中药。比方:人参、党参、当归、鹿茸……。因为我的姐夫在福州,是买卖药材生意的商人。当时,我认为:与其参加中国人杀中国人的战争,不如远离战争,做中医药的生意好。不但心安理得,而且,问心无愧。
我1948年在扬州结婚。我老婆家都主张我在上海发展。
当时,在浙江的部队一找我,我就到福建去了。兵荒马乱的谁也不管谁了。
全国解放时,我在福建。我的户口是从上海转到福建的。我在福建生活的不错,解放初期也登记了。但是,福建派出所的警察们对我很好。我还是做我的中医药生意。
1958年,浙江永康的警察来了。拿出逮捕证,给我当上手铐。押送原籍。从1958年到1964年,我一直在浙江金华蒋堂劳改农场。逮捕后,我的上海老婆和我离婚了。她带走儿子,女儿留给我家。从此,我孑然一身。
等我1964年从监狱放出来不久,刚刚好遇上文化大革命。人们蜂拥而至到我家抄家,一次,两次、数次。挖地三尺,全部拿去。有在国民党抗战部队发的中正剑、呢子军装,缴获侵华日军作为留念的军帽、军旗。黄埔同学会的通讯录、照片、奖章、帽徽,等等。
当时,造反派说是黑的就是黑的,说是白的就是白的。不能申辩,一申辩马上打人。
我问姚福卿都申辩些什么内容了?
姚福卿说:“我当时申辩,我一天没有和共产党打过。抗战胜利,我就做生意去了。我们黄埔同学有几位去了共产党的部队,难道让我和他们打仗吗?——马上是拳脚相加!”
我在狱中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已经摘了。等我出了县大狱,又给带上了。
姚福卿回忆:我住的这个房子前面那间破房子,看见了吧?那时,住着一个黄埔16期的抗战老兵。参加过抗日战争,身上伤痕累累,军衔上校。他也是从县大狱放出来的,我们见面悄悄谈一谈人生幸福的回忆:“还是监狱里讲政策、讲人道主义。”我们都希望回去。
后来,黄埔16期的街坊上吊自杀了。
采访姚福卿是楼潘荣先生翻译,否则,我什么也不懂。没有小楼的帮助,我一筹莫展。
姚福卿家的小院子很是清静,房子是200年前的,老人是90年前出生的,只有姚福卿的外孙是新生代,80后;姚福卿的外孙的儿子是刚刚出生的,他是个活泼好动的小孩子。
姚福卿家的院子里没有桌子,我在板凳上记录。姚福卿的女儿给我们倒上喝的水,一会儿,水杯上落满了苍蝇。凳子上摆一些水果,一会儿,就被玩耍的小孩子碰翻在地上,满地翻滚。
采访姚福卿,使我想起许多往事来。我1984年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1987年在日本大使馆领事部工作。当时,北京的日本大使馆、英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澳大利亚大使馆、加拿大大使馆等国家的领事部是热闹的地方,天天人满为患。
很多中国人希望到外国去,很多中国人(其中不乏佼佼者)都希望加入外国的国籍。
我在日本大使馆领事部工作,常常见到这样的事情:中国的年轻女孩子下嫁日本国的老头子。双方由于不会外语,我还要帮帮他(她)们。
在使馆工作,我最大的体会是:从来没有见到外国人争着抢着加入中国国籍。有个说相声的大山,他是姜昆的徒弟,是加拿大人。不知道他是不是加入中国的国籍了?
采访中国抗战老兵姚福卿,又使我联想到我在日本国采访原侵华日军老鬼子们的情景:
日本老兵一般社会稳定,他们有“①,有年金(退休金)、②,有天皇的恩给(大政时代就有的国策)、③,有遗组会给的慰问,④,有政要的参拜。”日本老兵曾经参加太平洋战争、亚洲各国的战争、战役、战事,成为战俘以后,一般交战国都遵从日内瓦战俘公约,使日本战俘受到良好的待遇。
唯独前苏联,把日本战俘押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据说,有1/3的日本战俘死在那里。
多少年来,日本老兵的生活不受各种日本党派、政体的干扰;不像中国老兵,只要是国民党老兵,就“胜者王侯败者寇”,为奴、为寇30年。日本老兵的生活非常静谧。
我也去过欧洲,那里也是静谧的田野和优雅的村庄。我想,如果给你们也套上“以阶级斗争为纲、残渣余孽、地富反坏、株连亲属;镇反、三反五反、大炼钢铁、自然灾害、四清四不清、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你们还能悠闲自得、优雅微笑吗?
姚福卿老人的家喧嚣过。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整整十年。
当然,德国也喧嚣过,但是,从希特勒死去后就趋于平静了。一静,就是66年。
意大利也喧嚣过,自此把墨索里尼倒着吊起来就趋于平静了。一静,也是66年。
日本当然也喧嚣过,什么原子弹呀,姚福卿呀,各种原因,日本老百姓也平静了。
战后66年,中国平静了多少年?姚福卿家是一面镜子,看看姚福卿就知道了。
姚福卿和小楼在姚福卿家大清帝国时代建的老宅子门口。姚福卿对腰伤三缄其口
90岁的姚福卿至今喜欢到田里去干活,田野里阳光明媚,充满了自由自在的空气
姚福卿自己种的地瓜,他在水塘中洗一洗,扒开皮,请我们吃
姚福卿的腰伤,是在什么情况下形成的?对我的提问他始终三缄其口,不愿意提及。我也不好意思死缠烂打的。我个人估计,没有七八个热血青年,三、四根棍子,可能,不能重新塑造出一个人的“新形象”来。姚福卿回答很抽象,他说,我上中学时就会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侵华日军要亡我中华民族,我挺直腰板、参加国军,我上最前线了。后来,永无抬头之日,我只求偷生;能偷生就好。从1966年到1976年,只要是不批斗,饭吃吃,我马上拿上锄头去田里干活。有空,我在田里看看书。村里冷嘲热讽的,不如劳改队好。 写姚福卿的时候,我刚刚好看到两篇文章。摘录如下,以解燃眉之急。何谓“燃眉之急”呢?姚福卿不愿提及,而有人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两篇文章的摘录,一篇是回忆共产党将军的,一篇是艺术家陈凯歌的回忆录。我想,有个这两篇文章,姚福卿的腰,就有了答案了。 2011年2月26日《文摘报》5版节选自:《贺龙冤案调查始末》 “文革”中遭迫害当时,贺龙和罗瑞卿主持军委工作,罗瑞卿被打倒后,林彪把矛头对准了贺龙,从1966年8月起,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谣言便四处散播。1966年12月,周恩来将贺龙夫妇保护在西花厅。由于林彪下决心要打倒贺龙,周恩来不得已决定将贺龙夫妇送走。贺龙夫妇被送到卫戍区一师驻地西山象鼻子沟,外面有解放军一个连保卫。1967年,由康生担任组长,叶群为副组长的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专案组将被褥、枕头全部收走,贺龙夫妇只能睡在没有卧具的床上,用手臂当枕头。此后,专案组又借口水源困难,断水45天,每天只有一小壶饮水,其他用水只能接雨水解决。在中共九大上,林彪唯一副主席的地位得到党代表大会的确认。他开始肆无忌惮地迫害贺龙,贺龙的处境更加困难,身体越来越坏。1969年1月,专案组规定收缴贺龙自备的药品,强令他们搬家,离开周恩来安排的住地。贺龙的糖尿病急剧恶化,6月8日出现酸中毒,却注射葡萄糖,6月9日死于301医院。如果没有上级的指示,医生是不敢注射葡萄糖的。为了掩盖罪责,贺龙住院,不准其夫人薛明陪同。第二天,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召开会议,说:贺龙的死亡报告“要写得详细”,“专门有医生照顾,我们尽到了责任”。 陈凯歌在《少年凯歌》一书中有这样的回忆: 到了五月桃李缤纷的时候,母亲却突然把我叫到身边。我不见父亲已经很久。他曾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一年,回来变了一个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兴,买了钢笔作礼物,又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勉励的话。不久前,他和许多人一起去学习,住在一个地方叫社会主义学院。母亲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犹豫了一下说:“你去看看爸爸。把这个带给他。告诉他,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要相信党。你回来我再跟你谈。”母亲当时抱病在家,她患心脏病已有十年。我点点头。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怎样骑过柳絮飘飞的街道,思绪像阳光下的景物一样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发涩,耳边总是母亲的声音:把问题同组织上讲清楚。——张老师的话并非没有根据。父亲确实有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将不一样。就像小时候举起存钱的瓦罐,“啪”地一声摔得粉碎,硬币滚了一地。
社会主义学院是一座大楼,我是在门前的传达室中见到父亲的。比起刚从农村回来,他竟有憔悴了许多。我把母亲的话转达给他,大概使他很难堪,他沉着脸,许久才说:“告诉你妈妈,我的问题早已向组织上交代过了。我没有新的问题。我相信党。你要照顾妈妈。妹妹好吗?你要好好学习。”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我希望我当时抱过他一下。
在看过父亲后的那个春夜,我从母亲那儿得知,父亲在1939年19岁时,参加过国民党。这是成人间的谈话,母亲和我灯下诵诗的景象已经显得遥远。母亲解释说,父亲参加国民党,完全出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爱国热忱。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来自东南沿海的父亲甚至没有听说过共产党。她在头一次对我讲起抗战后反对国民党腐败的经历之后说:“这件事组织早有结论。这是历史,你没有经历过,不容易懂。今天告诉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亲的话,不愿接受这个事实。
我开始恨我父亲。一天深夜,我被突然惊醒,院子的大门外是一片愤怒的人声和猛烈的击门声。——在一次红卫兵行动中,一位住在院子里的革命烈士未亡人,因被指为“黑帮分子”,而被抄家。烈士的遗像被红卫兵用刺刀划开。而也是红卫兵的烈士之子得到消息之后立即聚集了所在大学的红卫兵们,包围了这座院子。两扇造于清代的红漆大门在午夜后被守门人锁上,以防意外,竟被人力生生推倒,与此同时,上百红卫兵踏着轰然倒地的门冲了进来,挨家搜查划破遗像的“阶级敌人”。烈士的儿子悠闲地抱臂而立,身边围满了求情的妇孺;其他人,有男有女,晃动手电,挥舞皮带,对所有的居民怒声相问,孩子也不放过。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手持刺刀,声音喊叫到嘶哑,像一块烧红的铁似地要“以血还血”。他们在扮演完强徒、法官和刽子手的三重角色之后,于黎明前离去,遍地狼藉。
父亲被押进院子的时候,我正站在门口的人群中。有戴着红袖章的人在场,今晚会发生什么,是不用猜的。不知是夜色苍白还是人更苍白,他看上去像个影子,和其他许多影子走在一起。
这个院子的西翼,大都住的是人们都知道的艺术家。下午,我和其他孩子已经在各自的门楣上贴了侮辱性的对联,词都是我写的,为了迎接各自的家长。批判会是在住宅楼背后召开的,父亲和其他人站在背后窗内射来的淡淡灯光里,一排地弯着腰。不久前还同他们一起工作的工人们开始批判他们,从政治问题一直问到他们吸的香烟的等次。父亲的名字被叫到的时候,他的头更低了下去。他的头衔是“国民党分子、历史反革命、漏网右派”。人群中响起“打倒”的口号声。我也喊了,自己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很大。
整个情形恍如梦境。戴红袖章的人叫到我的名字。我在众人的目光下走上前去。我已经记不清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父亲看了我一眼,我就用手在他的肩上推了一下,我弄不清我推得有多重,大约不很重,但我毕竟推了我的父亲。我一直记得手放在他肩上那一瞬间的感觉,他似乎躲了一下,终于没躲开,腰越发弯了下去。四周都是热辣辣快意的眼睛,我无法回避,只是声嘶力竭地说着什么,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很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十四岁。但是,在十四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我强忍着的泪水流进喉咙,很咸,它是从哪儿来?它想证明什么?我也很奇怪,当一个孩子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听到的仍然是笑声,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民呢?
中途我回了一次家。母亲躺在黑暗中的床上,嘴唇紧闭着,仿佛正有一把刀放在她的脖子上。她轻轻对我说:你去吧。
那一夜,是我第一次和我已经背叛了的父亲躺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直到第二天早上,他也没有对我说什么,我怕见到他,他的目光闪烁着,也怕见到我。我听不清母亲在卧室里对他说了什么,灯随后熄灭了。……,……。火一直烧到深夜才熄灭。我的同学们拿走了从闹钟到照相机的所有财物,甚至治头痛的风油精,据说后来交给了制片厂的造反派。他们离开时竟然个个庄严地依次同我握手,仿佛他们才把我从歹徒手中拯救出来要通过这握手得到当然的感激似的。我走进家门,屋里像一个刚刚呕吐过的胃。第二天早上,奶奶扫起残灰。过了火焰的槐枝已经枯焦,地上的方砖有几块现出裂纹,缝中的灰烬在秋风过后才被吹净。我和奶奶把垃圾箱抬到大门外,纸灰飘起来,久久不落下。
在我家被抄后不久,我的红卫兵同学们的家大都相继被抄。其中一些情景的惨烈,又大大超过我的遭遇,这又是他们决没有想到的。
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范围内有总数几百万以上的家庭被抄,有的知名人士家竟反复被抄几十次,白天黑夜击门声不绝于耳,真正是片瓦无存。同时,被抄者的子女沦为盗贼乞丐者则比比皆是。在抄家过程中,保存于私人之手的历代文物书画扫荡一空,大部分焚后扬灰,小部分烂霉于库房,多少年后流失海外,面目不可复识。……,……。一九六七年,革命已经退潮。红卫兵早已不是时髦;学校复课遥遥无期。父亲仍然被关在制片厂的“劳改组”中,他的问题仍然是耻辱的印记,像一块烫伤一样碰不得。抄家那天的情景,在母亲和红卫兵面前的双重羞愧,使我像一棵树,太小就被一刀砍翻,断开来向着世界。我已经知道世界怎样看我,怎么对待它就是我的事。我不是任何组织的成员,闲着没事,就回到旧日的业余体育学校,这里已经没有人负责,负责的就是我们。我和过去的队友每天打球、游泳,再就是抓流氓。
屋子里满是少年。他被带进来的时候眼神很惊慌。有人看见他在水里摸了一个妇女的乳房。是不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需要有人扮演一个注定失败的角色,不然这出戏就演不成。
我们都靠墙站着,和他一样都只穿着游泳裤。屋子中间的空间都是他的。一开始我就听见自己的心跳声,我的太阳穴变成了一面铜锣,“砰砰”地敲响着。我的一个朋友走过去,手背在后面,笑着低声问了一句什么,他想回答的时候,朋友的拳头已经打在他的脸上。他倒下去。他被喝令站起来。他站起来,脸上有一块发白。他还未站稳,又被一拳打倒下去。他再次被喝令站起来,另一个人向他招招手,他走过去。这一拳打在他的下巴上,他倒退了几步。第二拳,第三拳;然后,他开始像一只皮球一样滚来滚去。起初,我站着,只看见我的胸膈膜下有一块在“突突”地跳,跃跃欲试又胆怯着。我还没有打过人。我走过去;他已经被另外的人打倒。我退回来;再走过去,一拳打在他的脸上。他的颌骨撞疼了我的手,他无动于衷。我被他的无动于衷激怒了,冲过去用力地抽他的耳光;我两眼发黑,浮起一圈一圈的金色,手上的感觉像打在一匹马背上;直到许多人冲过来抱住我。我的手掌发麻,心跳快得站不住脚,大口地喘着气。我在阳光下躺了很久,睁开眼睛时天蓝得不敢细看。
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察觉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就像水倒进一只浅浅的盘子。我在六岁那年蹲在葡萄架下,看着一只小鸟抽搐死去所种下的种子,终于有了结果。 姚福卿的乡村诊所是经过县政府批准的合法医疗机构
姚福卿对跌打损伤、腰肌劳损有独特的医疗方法。远近闻名。
姚福卿家就是一个乡村的医院,方圆数公里的男女老幼都来就诊。
抗日战争胜利后,姚福卿就受亲属的影响关注中医中药。他不参加内战,却穿着军装在上海至福州的铁路线上倒腾中药。1964年,他从县大狱放出来了,为了苟且偷生,为了活着,他在不被批判的日子里不言不语,每天只到田地里种地、看医书。
改革开放活,他又开始了他的乡村行医的生涯。在他外孙家的一楼,他和女儿开了一家诊所。在浙江农村开诊所是要经过严格审批的,姚福卿父女是经过地、县两级医疗资质审批才通过检查合格的。我在姚福卿家采访三个半小时,看见来了7位病人。一位,是天天需要打吊针输液的病人。他的输液液体是大医院领取的。有三个病人是跌打损伤、腰痛、颈椎疼痛。有三个病人是伤风感冒之类的病痛。
我问了问这些病人,为何而来?为什么不到县城的大医院去?
他们回答:近。慕名而来。信任。便宜。方便。实惠。管事。……。
有个陕西西安在浙江打工的小伙子已经来了十几次,他的病情是腰扭伤。来前已经行走困难,经过姚福卿的治疗,他已经能重新劳动了。我特意给他们拍摄了一张治疗中的照片。
我一直希望日本记者和我一起重访浙江永康、浙江天台的抗战老兵。
我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工作的时候,就知道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程序:外国记者先向我国各级政府提出申请,再经过各级政府批准后,再经过被采访者的允许的情况下,一般,是可以进行采访的。
日本《北海道新闻》出版过一本叫《战祸的记忆》的丛书,就是千百个经历战火日本的老头子、老太太回忆战火纷飞的。日本人民是反对战争的,反思是在日本民间进行的。
《战祸的记忆》中,有《北海道新闻》记者在卢沟桥上对中国八路军老战士赵忠义老人的采访。刚刚好,是我翻译的。在《战祸的记忆》一书中,除去“日本鬼子”词汇没有使用外,其他内容与八路军老战士赵忠义在卢沟桥上的自述相同。
下面,是我曾经对赵忠义的采访。
赵忠义,1919年生人,老家在河北省邢台的隆姚县东冬村,他1938年参加八路军,在县政府里当税务员。
1940年阴历11月26日,侵华日军鬼子兵突然把村子包围了,抓了他们七个八路军,在押往隆姚宪兵队的途中县委书记张春玉就叛变了。在邢台监狱,鬼子把其余不投降六人手脚捆住,先是灌辣椒水又是坐老虎凳,最后是压杠子----。“六个日本鬼子站在杠子两边,我痛的一下就昏死过去-----,他们拿咱中国人不当人呀!”老汉浑身哆嗦着,终于忍不住哭出了声。
“夜里两点,鬼子们来提我们,大家都互相点点头,知道是被拉出去枪毙的。谁知鬼子把我们押到北京的炮局胡同日军北平陆军监狱后,判了大罪,当时就加上了沉重的脚镣和手铐。”监狱里有工人、学生、职员,都是抗日份子,我们牢房里还有一名会日语的。监狱里每天吃两顿饭,一天放一次风,鬼子不许我们说话,对说话的人一律严刑拷打。我在炮局日军监狱关押了两年六个月,天天在牢房里做鞋子,稍有慢点就挨打。日本兵每天早晨查房,谁如果生病了,马上拖出去。拖出去的病号十有八九回不来。难友们都说:“隔离房就是死亡房,不给吃喝人能不死亡吗?” 我们牢房有三十几位难友,两年不到有一半儿人死难了。
1943年冬,我们一百多人被押往停泊在天津塘沽港的货船上,走了七天,到达日本国福岛。从此,开始了漫长的劳工生涯。 “在福岛三个月,每天扛木头,饥寒交迫,加上日本工头强迫下的重体力劳动,劳工们相续死去。
赵忠义说最为严重的一次是在北海道集中营,由于饥寒交迫和超负荷劳动,他们屋里七个人都患了病,吐血、尿血,日本人管都不管。那六位劳工都相续死亡了。后来,我们转到日本国北海道的置户村集中营服苦役,每天背石头,筛沙子。饥饿难耐,有几个劳工吃野菜和树皮中毒死去。-----天太寒冷,我把毯子捆在上身,外面再捆上蓑衣。双腿捆上水泥袋子,走起路来“哗啦、哗啦作响”,就这样熬过一个个寒冷的日子。后来,我们这批劳工从北海道到长野,又从长野到福冈当苦力。途中我们经过美国人在广岛上放的原子弹现场,只见一望无际的废墟,汽车都烧成铁疙瘩-----,好几天了,天空中的尘埃都伸手可接,黑色的!我知道:——快解放了!
“日本投降后不久,我们这批劳工终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回到魂牵梦萦的家乡。家人相见,抱头痛哭,爹娘都说:自打1940年你被日本鬼子兵抓走,我们都以为日本鬼子已经把你们杀害了,因为,你们都是八路军呀!”
“回国不久,我就参加了解放军,在四纵队36团12旅,是聂荣臻的部队。在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中我立了功。1950年我们杨得志兵团开往朝鲜前线,参加抗美援朝的战争,在战斗中我立功三次。”
赵老汉说:“听说有人占了咱们国家的岛屿,只要国家允许,我还要拿起枪上前线去,绝对不能让外国侵略者占领我们祖国的一寸土地!”我听了以后很辛酸,我说:“老赵哇,腐败干部的一餐饭,就是你们全家八口一个月的生活费呀!如果,外国侵略者来了,你还要上战场吗?”赵老汉眉头都没皱一下,说:“如果侵略者还敢来,我还要拿起枪,上战场!就因为我当过亡国奴,我当过牛马不如的劳工。”
我希望日本记者传达给日本人民些什么思想呢?
其一,中日友好不是满纸的空谈,是“重温历史,开创未来”的过程。
其二,像浙江永康的姚福卿老汉都是抗战的中坚了,日本占领中国谈何容易?
其三,中国的抗战老兵都是什么样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历史?
其四,中国浙江是工业极度发达,而农村极度落后的地区。
其五,是中国民众对于抗战历史的态度。
其六,中国人之间为敌,使得侵华日军“蚌埠相争、渔翁得利。”
2011-3-3
页:
[1]